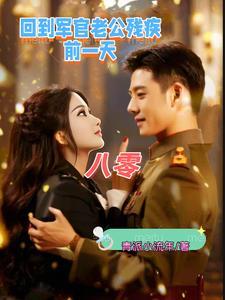紫夜小说>老街画 学生作品 > 第103章(第1页)
第103章(第1页)
夜渐深,画室里只剩下均匀的呼吸声,和那本摊开的旧画册一起,在月光里,静静诉说着未完的故事。
冬炉温酒时的絮语与画框里的长情
冬至的雪落了半宿,清晨推开社区美术馆的门,整座老街都裹在蓬松的雪被里。
赵念安踩着及膝的积雪从外面跑进来,棉靴踩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手里捧着个保温桶,哈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成转瞬即逝的雾团:“林叔叔,江叔叔,张奶奶熬的羊肉汤,让我趁热送来!”
林漾正蹲在壁炉前添柴,松木在火里噼啪作响,把他的侧脸映得泛红。“快进来暖和暖和,”他接过保温桶,指尖触到念安冻得发红的耳朵,“不是让你戴耳罩吗?这孩子,总不爱听劝。”
江辞从里间走出来,身上披着件厚羊毛毯,手里拿着两幅装裱好的画。“刚把《冬雪归人》挂好,”他指了指客厅的墙面,画里的青石板路上,两个身影踩着雪往美术馆走,手里提着盏灯笼,光晕在雪地上洇开片暖黄,“你看这灯笼的光,像不像去年我们去山里写生时,村民家挂的那盏?”
念安凑近看画,突然指着画里的细节笑:“江叔叔,你把林叔叔的围巾画得歪歪扭扭的,像只偷喝了酒的猫。”
林漾拍了下他的后脑勺,脸上却带着笑意:“那是被风吹的。”他转身去厨房找碗,留给江辞一个温柔的背影——这几年他眼角的细纹深了些,却更添了几分温润,像被时光仔细打磨过的玉。
江辞的目光追着他的背影,冰蓝色的眼睛在炉火映照下格外亮。等林漾端着碗出来时,他伸手接过,顺势握住他的手腕,指尖在他手背上轻轻摩挲:“手还是这么凉,过来烤烤火。”
两人在壁炉前的地毯上坐下,念安盘腿坐在对面,捧着碗羊肉汤小口喝着。汤里的萝卜炖得烂熟,混着羊肉的醇香在空气里漫开,和松木的烟火气缠在一起,成了最踏实的冬日味道。
“沈先生他们今天到吧?”林漾舀了勺汤,吹了吹递到江辞嘴边,“昨晚发消息说,温先生特意带了瓶二十年的花雕,要在院子里温着喝。”
“说是十点左右到,”江辞张口接住,舌尖尝到点淡淡的姜味——是林漾特意加的,知道他冬天胃容易凉,“还说给念安带了副新的滑雪板,让他去后山试试。”
念安眼睛一亮,汤勺差点掉在地上:“真的?去年去滑雪场摔了八次,沈先生还笑我是‘雪地里的企鹅’!”他放下碗,拿起画笔在速写本上画起来,“我要画张‘雪地逐鹿’,等他们来了给他们看,证明我进步了!”
壁炉里的火越烧越旺,把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随着树枝的晃动轻轻摇曳。林漾靠在江辞肩上,听着念安絮絮叨叨讲西北的见闻——新疆的向日葵花田有多辽阔,甘肃的老水车转起来有多壮观,陕西的窑洞冬暖夏凉,绣娘的指尖比画笔还灵巧。
“温先生教我用全站仪测绘老窑洞,”念安的笔尖在纸上沙沙游走,“说古建筑的每个角度都藏着古人的智慧,就像王爷爷修鞋,针脚歪一分都不行。”他突然有点不好意思,“沈先生说我的画多了些‘筋骨’,不像以前总飘着。”
江辞揉了揉他的头发:“那是因为你走的路多了,脚底下有根了。”他看向林漾,眼里带着藏不住的笑意,“就像当年你总说我画的山太硬,后来去黄山住了半个月,回来画的石头就带着云雾气了。”
林漾想起那些日子,两人挤在山顶的小客栈里,裹着同一条棉被看日出,江辞的手冻得发僵,却还是坚持把晨光漫过山峰的瞬间画下来。画纸上的笔触确实生涩,却带着股不肯妥协的执拗,像极了那时的他们——年轻,热烈,相信只要握紧彼此的手,就能走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对了林叔叔,”念安突然想起什么,“沈先生让我问你,要不要把你的《巴黎记忆》系列放进明年的跨地域展,他说那些画里的乡愁,和西北老街区的孤独特别像,能撞出有意思的火花。”
林漾愣了一下,那些画被他收在库房最深处,已经很多年没动过了。画里有塞纳河畔的落日,有蒙马特高地的风车,有留学生公寓窗外的梧桐,更有深夜里对着空白画布思念江辞的自己。那些笔触里的孤独与牵挂,确实和西北老街区的苍茫有几分相似。
“等沈怸来了再说吧,”他轻声说,“有些画,得等心境对了,才好拿出来见人。”
江辞握住他的手,指尖在他无名指的向日葵戒指上轻轻摩挲。那戒指戴了快二十年,边缘已经磨得光滑,却依旧牢牢地嵌在指根,像成了身体的一部分。“我陪你一起整理,”他低声说,“就像当年你陪我改那幅《老街初雪》,改到天亮。”
十点刚过,院门外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念安第一个冲出去,果然看到沈怸和温叙从越野车上下来,车顶上还堆着滑雪板和大包的行李。沈怸穿着件焦糖色的羽绒服,头发比去年白了些,笑起来眼角的纹路却比年轻时更温柔;温叙依旧是一身利落的深灰大衣,手里拎着个精致的木盒,不用问也知道是那瓶花雕。
“冻坏了吧?”沈怸给了林漾一个拥抱,拍了拍他的背,“比去年见你又清瘦了些,是不是江辞又没好好管着你?”
温叙则把木盒递给江辞,笑着补充:“特意找朋友淘的,说是埋在绍兴酒窖里二十年,温着喝最养人。”他看向跑前跑后的念安,“滑雪板在后备箱,下午去后山,我教你怎么刹车,别再像企鹅似的打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