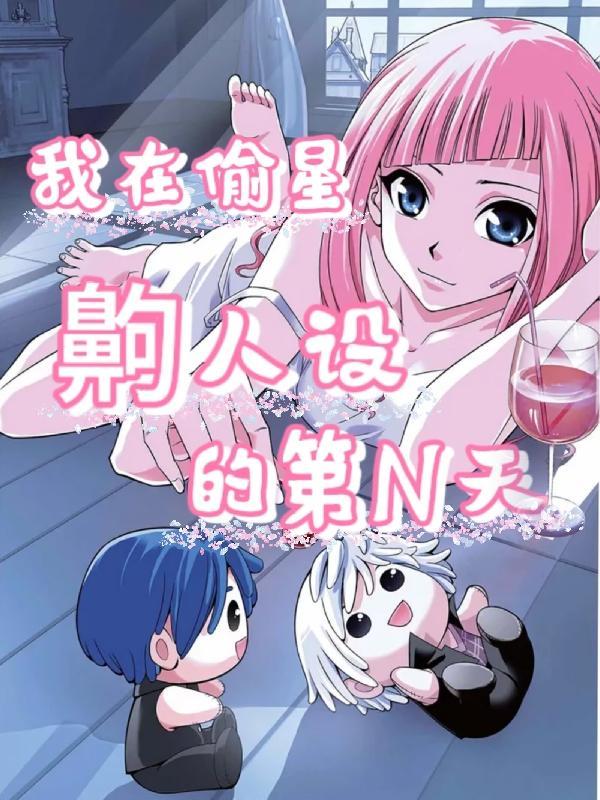紫夜小说>锦绣连城_云里的伞 > 洪水(第1页)
洪水(第1页)
洪水
许连城端起自己面前的茶杯,温热的水汽模糊了她的眉眼。
她没看寻影,指尖划过杯壁上的冰裂纹:“劫走的人,有踪迹吗?”
“对方手法干净,只在苏州城外留了个标记——是片柳叶。”
寻影顿了顿,补充道:“像是江湖上的路数,但出手极有章法,不像是寻常盗匪。”
柳叶?
许连城指尖微顿,眸色深了深。
她放下茶杯,杯底与案面相撞,发出一声轻响,在寂静的殿中格外清晰:“剩下的一半,按原计划送进密仓,加派三倍人手看守。”
许连城转过身,目光落在案上那杯未动的热茶上,眸色复杂:“你退下吧。”
“是。”
寻影应声退去,殿门合上的刹那,许连城才缓缓拿起那杯茶,指尖触到微凉的杯壁,像触到了什麽遥远的记忆。
她记得有人曾在暖阁里对她说:“连城,廉州水患凶,若是提前备足粮草药材,百姓就能少受些苦。”
那时阳光透过窗棂,落在那人低头的发顶,温柔得让人心颤。
这一世,她提前动了手,却没想到半路杀出程咬金。
是谁?
许连城将茶杯凑到唇边,热茶的暖意漫过舌尖,眼底却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涩意。
她轻轻吹了吹茶沫,烛火在她眼中明明灭灭,像藏着一场无人知晓的博弈,也藏着一段不敢轻易触碰的过往。
夜色更深了,而廉州的风雨,已在千里之外悄然酝酿。
几日後的朝堂果然如那夜的烛火般,在暖风和煦中透着几分不察的滞涩。
距离廉州那场注定要来的洪水尚有一月,紫宸殿的朝会依旧循着旧日章程,官员们奏报着春耕丶漕运,无人提及南方的云气已悄然变了颜色。
巳时过半,卫锦绣随父亲卫胜踏入上书房时,殿内正飘着淡淡的松烟墨香。
许铮放斜倚在铺着明黄色软垫的楠木椅上,手中捏着一本江南漕运账册,见他们进来,只擡了擡眼皮:“卫将军父女今日同来,倒是稀客。”
卫锦绣垂眸行礼,声音清润如溪:“回陛下,臣女近日翻查旧档,见去年冬雪消融得早,入春後江南雨水似比往年稠些,廉州地处低洼,依着往年经验,怕是汛期会来得急些。”
许铮放翻过一页账册,笔尖在“漕粮损耗”处顿了顿,漫不经心道:“往年不也这样?江南水乡,多雨是常事,只要堤坝撑得住,便无大碍。”
他指尖敲了敲账册:“比起这个,朕更忧心漕运的损耗,去年竟比前年多了三成。”
卫锦绣指尖微蜷,她早料到皇帝会如此,毕竟廉州堤坝稳固了十馀年,太平日子过久了,谁会把一句“或许多雨”放在心上。
她擡眸时眼底已漾起温和笑意:“陛下说的是。”
“只是臣女想着,如今北境战乱已定,百姓刚归田亩,最忌天灾,廉州堤坝关乎下游三州百姓生计,若能趁汛期未至前去检修一番,补补缝隙丶固固堤脚,便是花些人力物力,也比真出了纰漏再补救强。”
“臣女愿往廉州走一趟,一来替陛下看看堤坝实情,二来也能体察民间疾苦,也算为民生尽份力。”
卫胜在旁适时补充:“陛下,锦绣自小跟着夫子看些水利图谱,对堤坝构造略知一二,她去倒是妥当。”
家中四个儿子都已经有了功绩,卫胜不愿意让女儿冲锋陷阵,若是揽了这个差事,出去游玩一趟,回来得些嘉奖也是不错的。
还省得这丫头,天天念叨要去边疆驻守。
许铮放这才放下账册,打量着眼前亭亭玉立的少女。
卫锦绣自小沉稳,比同龄女子多了几分远见,战乱时曾帮着卫胜筹算过粮草,确有急智。
他沉吟片刻,颔首道:“你说的有理,民生确实是眼下要务,便准你去,带些工部的匠人,粮草银两从户部支用。”
话音刚落,门外便传来一阵清脆的环佩声,穿藕荷色宫装的许连城提着裙摆闯了进来。
发间金步摇晃得人眼晕:“父皇!儿臣听说锦绣姐姐要去廉州?”
她走得急,脸颊还泛着红晕,见许铮放点头,立刻笑道:“那儿臣也要去!廉州离京千里,儿臣还没去过江南呢。”
“再说了,父皇常说皇家要知民间冷暖,儿臣跟着锦绣姐姐去,亲眼看看堤坝怎麽修,百姓怎麽过日子,回宫後讲给父皇听,岂不是比奏章上的字儿更实在?而且皇家亲自去体察民情,百姓见了定当觉得父皇心系他们,民心不就更稳了?”
许铮放本就疼这个小女儿,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又想着廉州此时应是草长莺飞,气候温润,让她出去散散心也好。
![外挂已到账[末世]+番外](/img/13860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