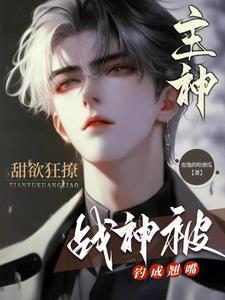紫夜小说>四合院十三岁的我被大领导召见 > 第842章抵达英国(第1页)
第842章抵达英国(第1页)
四合院的堂屋被收拾得格外亮堂,八仙桌上摆满了菜——顾母亲手炖的红烧肉泛着油光,刘母做的糖醋鱼翘着尾巴,周姥姥蒸的糯米丸子堆得像座小山,还有顾爷爷特意让人捎来的卤味,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
顾从卿坐在主位旁,左边是刘春晓,右边是土豆,身后的墙上还贴着他和春晓的结婚照,照片上的人笑得眉眼弯弯。
“从卿啊,到了英国,可别学那些洋人喝生水,自己备个暖壶,天天烧热水喝。”
顾母往他碗里夹了块排骨,絮絮叨叨地叮嘱,“那边冬天冷,我给你缝的棉背心记得穿,别冻着。”
刘父端起酒杯,跟他碰了碰:“出去了代表的是国家,说话办事得稳重,既要守住原则,也别太死板,遇事多跟驻英的老同志商量。”
“爸说得是。”顾从卿仰头喝了半杯酒,酒液下肚,暖烘烘的,“我都记着呢。”
周姥姥眼睛不好,却准确地摸到一碟花生,往他手里塞:“这是你爱吃的盐炒花生,我装了两小袋,路上饿了垫垫。
到了那边要是想家,就闻闻咱这花生味儿,跟家里的一样。”
土豆扒拉着碗里的饭,忽然抬头:“哥,你到了英国,能给我寄明信片不?
就要印着大城堡的那种!”
“能,”顾从卿笑着揉了揉他的头发,“不仅寄明信片,还给你寄巧克力。”
刘春晓一直没怎么说话,只是默默给他夹菜,把他爱吃的青菜都堆在碗边。
直到顾从卿的看向她,她才低声说:“到了就给我写信,哪怕就几句话呢,我也放心。”
“一定。”顾从卿握住她放在桌下的手,指尖传来她的温度,“等我站稳了,就申请让你去探亲。”
周姥爷最后开口,声音洪亮:“出去了好好干,别给家里丢人,更别给国家丢人。家里有我们,不用惦记,照顾好自己,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孝顺。”
“是姥爷爷。”顾从卿起身,给满桌长辈都敬了杯酒,眼眶有点发热。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照着窗纸上的“囍”字,屋里的笑声、叮嘱声混着饭菜香,像团暖烘烘的棉花,把离别的伤感都裹得软了些。
顾从卿知道,这一桌子菜,满耳朵的叮嘱,都是家人沉甸甸的牵挂。
顾从清夹菜的手顿了顿,目光落在土豆安静吃饭的侧脸上。
这孩子今天格外乖,一碗米饭快吃完了,嘴角沾着点酱汁也没像往常那样咋咋呼呼地叫人擦,只是自己用手背蹭了蹭。
“哥,英国的城堡是不是比画册上还大?”
土豆忽然抬头,眼里闪着光,没有了往日的黏糊劲儿,语气里多了份好奇。
“应该是。”顾从卿笑了笑,往他碗里放了块糖醋鱼,“等你放暑假,我给你拍照片寄回来。”
“嗯!”土豆用力点头,低头继续扒饭,没再像以前那样缠着问“哥你什么时候回来”“能不能带我一起去”。
顾从卿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蛰了一下,有点酸,又有点说不清的欣慰。
上次他下乡,土豆抱着他的腿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嗓子都喊哑了。
每次离家,这小子都要偷偷跟到直到看不见人影才抹着眼泪回去。
可今天,他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规规矩矩地跟长辈们打招呼,甚至还会主动给姥姥夹块软和的豆腐。
那股子孩子气的依赖好像一下子收起来了,露出点小大人的模样。
“土豆懂事了啊。”刘母笑着夸了句,“知道哥哥要去干正事,不胡闹了。”
土豆腼腆地笑了笑,没说话,只是又往顾从卿碗里夹了一筷子青菜。
顾从卿拿起筷子,夹起那块青菜慢慢嚼着,心里五味杂陈。
原来孩子长大真的是一瞬间的事,好像昨天还在怀里撒娇要糖吃,今天就已经能站在旁边,安安静静地送你走了。
他忽然有点怀念那个会哭会闹、抱着他脖子不肯撒手的小不点,可看着眼前这个眼神清亮、努力装镇定的少年,又忍不住想,这样也好,长大了,就少些离别苦了。
饭快吃完时,土豆忽然凑近他,小声说:“哥,我给你叠了一沓千纸鹤,放你包里了,书上说这个能保平安。”
顾从卿心里一暖,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好,哥带着。”
原来不是不惦记,只是换了种方式。
这小子,确实长大了。
1977年的风里还带着些时代的拘谨,顾从清捏着那张印着“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票,指尖都有些发紧。
窗外的四九城机场跑道上,飞机正缓缓转动,引擎声闷闷的,像闷在鼓里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