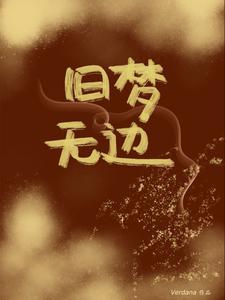紫夜小说>你不是朕的白月光 作者石门之客 > 第44章 第四十四章 修罗场来了(第3页)
第44章 第四十四章 修罗场来了(第3页)
“也罢,朝野纷争,林夫子不感兴趣,那就说些别的——”萧珣挑眉,转过话音,“不如,就说说林夫子关切的微民,生计之事吧。”
“萧公子是指——”
萧珣示意林榆坐下,促狭一笑:“这不,民以食为天。林夫子还没用过朝食吧?”
“萧公子怎麽知道?”林鸢偏头问。
“看林夫子的模样,眼下些许发青,想来是经历前夜之事,心有馀悸,这两日不曾好眠,衣上沾了寒露,想必是今日一早不见女弟,心里着急,风风火火赶来,连裘衣都不曾套上。”
萧珣目光向下扫去,“靴底沾了梅瓣,大概为了取近路,从梅林过来的。靴尖上有些青色,雪下卵石上多青苔,看来免不了是在薄雪上滑了一两次。”
他勾起唇角,“怎会有闲心用朝食?”
林鸢睁大了眼,不由地轻叹,萧珣对林榆“真是体察入微啊。”
萧珣扬眉笑道:“玩笑而已。其实,就是一句寻常寒暄罢了。哪会想那麽多?”
他屈指,想在林鸢头上作弄地一叩,刚要擡手,却见林鸢起身,拉了林榆入席,最终只是拈了拈手心。
林榆轻笑了一声:“说得都对。来得仓促,不修仪容,萧公子见笑了。只是,梅瓣不是来自梅园。阿鸢喜好梅花,插了数支在我的屋内。”
他说着,朝来到了面前的林鸢温柔笑了。
萧珣笑容倏忽黯淡。
他看向食案,不自然地继续寒暄:“对了,林夫子从长安来淮阳国多年,吃得惯淮阳国的饮食吗?”
“吃得惯。”
侍女前来添了杯箸,林榆不再推辞,接过了雁羹,吹开白雾:“在下年少时游历关中关东各地,不讲究饮食,什麽能吃。”
他停顿稍许,擡眼笑问:“萧公子不是也游历江湖吗?”
萧珣一怔,提起了银箸:“关中人多食粟黍,口味中庸。关东辽阔,多麦饭藿羹,琅琊胶州临海多水,喜食鱼脍,偏好鲜咸。可这淮阳国人,喜好花椒入馔,竟与蜀地相似,就连火锅,都是配的青芥酱与花椒酱。”
林榆闻言微愣,瞟向林鸢。
林鸢神色俨然不大自若,朝他吐了吐舌。
“是——”林榆登时心下了然,啜了一口茶,把一个“吗”字吞了下去,放下杯盏後,正色道,“花椒价贵,实则多为高门朱户所喜爱。在下一介平民,居于乡野之间,这样的稀贵之物,吃得倒是不多。”
萧珣看着案上的一盘花椒拌肉脯,兀自道:“王妃待客,格外用心,淮阳王又好奢靡。所以,所用的花椒,都是一粒一粒精挑细选的蜀椒。听说是冬日中,将田地覆了屋庑,昼夜燃蕴火,才反了季节时序,种出来的新鲜花椒。”
他的馀光看见那二人默契地相视一笑,林榆眉目之间,尽是化不开的温柔,手中筷箸忍不住敲了一下碗沿,“——因而更麻,更辣。我都不知该如何下口。又不好抱怨,省她好心办了坏事,反而惶恐。每日只能来你们听泉院蹭些东西吃。”
他接着朝林鸢笑道:“还是你做的,合我胃口。”
林榆轻咳了一声:“萧公子吃的那些,都是听泉院中李丶王两位阿媪做的。”
萧珣低头抿了一口茶,缓缓道:“那也是因为我和阿鸢的口味相仿吧。”
“李媪和王媪都是按着林榆和贺夫子的口味……”林鸢温吞插嘴。
林榆打断了她:“公子若是喜欢两位阿媪的羹馔,不如——”
萧珣弯了唇角:“——多谢林夫子相邀,我自会常往。”
林榆报之一笑:“我是想说,不如让两位阿媪到东苑来。她们二人,正因淮阳王府收留,施以饮食医药,无以为报,终日诚惶诚恐呢。若能前来照拂王府中的贵客,她们定然喜不自胜,淮阳王与王妃想必也绝无不许之理。除了做饭食,若说起淮阳民风民俗,她们二人来自本地,定也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林鸢埋头在林榆吹温了的雁羹之中,听了这话,笑得不慎呛了一口。
萧珣仓促地倒了杯茶,刚想伸手递过去,却见林榆已经拍着林鸢的背,帮她顺气。
林鸢呛得脸色通红,唇角沾了些残羹。她自感失仪抱歉,朝萧珣侧开了脸。
“擦擦吧。”三个字没说出口,生生咽了下去。
只见林榆另一只空着的手,抽出了一方帕子,为她轻轻拭着。
那帕子上绣着兰草,并不精美,却能看出来是兰草。
萧珣手上捏着一方素帕,在食案之下揉得皱了。
而林鸢微扬着脸,半是撒娇,半是嗔怪,不知朝林榆嘟囔了些什麽。
他的眼中,只看得见她笑弯了眉眼,窗纱外的天光尽数泻在她的脸上。
是无忧无愁的模样。
酸意滋了牙。
林榆是阿鸢的兄长。是兄长。兄长。
他默默地对自己念了三遍。
终究还是别开了眼,怨气来到了银箸上。
受气的是面前的一盘剥了壳的鸡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