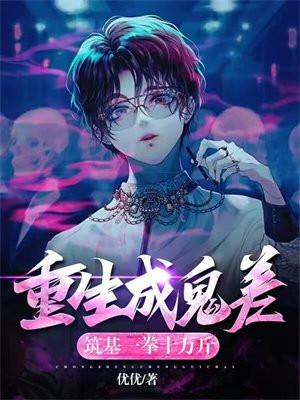紫夜小说>开局惊艳全场 > 第79章 她拆开档案袋时风从裂缝里进来(第1页)
第79章 她拆开档案袋时风从裂缝里进来(第1页)
“咔哒。”
一声轻响,仿佛是某个古老生物的关节在沉睡中被惊醒。
随着档案员戴着白手套的手指微微用力,第一只铁柜的柜门缓缓开启,一股混杂着铁锈与陈腐纸张的气息扑面而来,像是被压缩了三十年的沉默,在这一刻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苏霓站在一米开外,目光锐利如鹰。
她没有去触碰那些泛黄的牛皮纸袋,只是静静地看着。
赵小芸的镜头紧随其后,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但苏霓示意她保持距离,不要干扰档案员的工作。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近乎神圣的紧张感。
第一批解封的,是代号为“风筝”的系列监控报告。
每一份都详尽记录了某个特定人物在特定时间段的言行举止,从与谁通了电话,到在公园的长椅上停留了多久。
字里行间透出的那种无孔不入的审视,让在场的年轻实习生们不寒而栗。
然而,当档案员从最底层抽出一份用红色粗线捆扎的独立文件夹时,所有人的呼吸都为之一滞。
文件夹的牛皮纸封面已经脆化,但上面用宋体加粗印刷的八个大字却依旧触目惊心——《舆情风险人物分级名录》。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内部绝密,严禁外传。
苏霓心头一跳,走上前,亲自接过了那份沉甸甸的文件。
解开红线,翻开第一页。
一份精心设计的表格映入眼帘。
名单按照风险等级,被清晰地划分为红、黄、蓝三级。
蓝色是“需关注”,黄色是“需引导”,而红色,则是刺眼的“需管控”。
每一级下面,又细分出不同档位。
苏霓的指尖从那些名字上缓缓划过。
她看到了那个因在大学课堂上朗诵自己创作的长诗而被停课的诗人,他的风险等级是“红色二级”,处理建议是“限制公开表渠道,内部批判教育”。
她看到了那个因承包的土地被强占而屡次上访的中学教师,他的风险等级是“红色一级”,处理建议是“调离教学岗位,纳入重点稳控名单”。
她还看到了那位代表个体户群体,在听证会上直言税收政策不公的商贩,同样是“红色一级”,处理建议是“审查其商业往来,压缩其经营空间”。
名单上,红色一级,共计十七人。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被强行扭转的人生。
苏霓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一页一页地翻阅下去。
当她的目光落在最后一页最末尾的那个名字上时,她的指尖猛地顿住了,仿佛被一股无形的电流击中。
林素芬。
这个名字她太熟悉了。
在许文澜的身世调查中,这个名字是所有线索的,也是终点。
而在“林素芬”这个名字后面,备注一栏里,用钢笔手写着一行冰冷的蝇头小楷:“热衷于组织青年诗会,其作品在青年群体中流传甚广,思想内容具有煽动性。建议:限制其子女的社会流动性,以降低潜在的代际影响风险。”
“限制其子女的社会流动性……”
苏霓反复咀嚼着这几个字,一股寒意从脊背直冲天灵盖。
原来如此。
原来许文澜那份堪称完美的领养手续,那快得异乎寻常的审批流程,其根源竟在这里。
那不是一次充满巧合的“合规”收养,而是一场精心策划、自上而下的“风险剥离”。
她不是被“领养”,而是被“移除”了。
那个瞬间,苏霓终于明白了许文澜眼中那种深藏的、与年龄不符的疏离感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