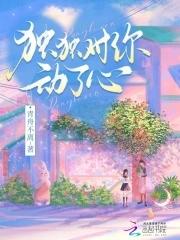紫夜小说>金戈作用好吗 > 第59章 刘秀昆阳之战破王莽(第2页)
第59章 刘秀昆阳之战破王莽(第2页)
观星台上的王邑终于慌了,他没想到刘秀竟能引动上古灵脉,忙下令九婴攻击龙睛山。九头蛇身的异兽咆哮着冲上山坡,水火齐喷,却被阵纹的金光挡住,根本无法靠近。“快!毁了阵眼!”王邑抽出青铜剑,亲自率修士冲上山,剑上的周礼符文与阵纹碰撞,出刺耳的摩擦声。
刘秀闭着双眼,对周围的厮杀充耳不闻,他的意识已与灵脉融为一体,能清晰地“看到”九环锁灵阵的脉络:昆阳的灵脉与骊山、咸阳的灵脉相连,当年秦始皇修长城时,曾用“玄铁”将天下灵脉连为一体,王莽的八门金锁阵不过是在这庞大网络上打了个结,如今这结被秦法符文解开,沉睡的巨龙终于苏醒。
“就是现在!”刘秀猛地睁开眼,双手将秦权和残片高高举起,“以我精血,引星落尘!”他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法器上,阵纹瞬间爆出刺眼的光芒,直冲天际。天空中的漩涡骤然收缩,无数陨石拖着长长的火尾,如雨点般砸向昆阳城外的新朝军队!
陨石的威力远想象。第一颗陨石落在八门金锁阵的“死门”,饕餮鼎被砸得粉碎,鼎中冤魂重获自由,化作金光消散;第二颗陨石砸中观星台,王邑的青铜剑被震飞,九婴的九头被陨石碎片击中,出凄厉的惨叫;后续的陨石如冰雹般落下,新朝军队的营垒被砸得粉碎,修士们的法袍在陨石的烈焰中燃烧,阵型彻底溃散。
“天谴!是天谴!”新朝修士们惊恐地尖叫着,丢弃兵器四散奔逃。九婴失去王邑的控制,在陨石雨中疯狂扭动,最终被一颗巨大的陨石砸中,身体炸成血雾。刘秀站在龙睛山顶,望着城外溃不成军的新朝军队,又看向昆阳城门——王凤正率军冲出城门,汉军的“汉”字旗在阳光下迎风招展,与天上的陨石火光交相辉映。
王邑在乱军中试图突围,却被刘秀的亲兵邳彤拦住。邳彤的环刀劈向王邑的法袍,周礼符文在法家煞气面前不堪一击,法袍瞬间破裂。王邑惊恐地看着邳彤染着灵气的刀刃,喃喃道:“不可能……周礼怎么会输……”邳彤冷笑一声:“不是周礼输了,是你逆天而行,断人灵脉,灭人法统,该败!”刀光落下,王邑的元婴被斩碎,尸体倒在陨石砸出的大坑中。
五、昆阳大捷
陨石雨过后,昆阳城外一片狼藉,新朝军队的尸体和残破的法器堆积如山,空气中弥漫着灵气灼烧后的焦糊味。刘秀率军下山时,汉军士兵正欢呼着清理战场,不少新朝降兵跪在地上,对着龙睛山的方向磕头,他们亲眼目睹了陨石天降的奇观,心中早已对王莽的“天命所归”产生了怀疑。
“文叔,这是从王邑营帐里找到的。”马武捧着一卷锦册走来,锦册上用金线绣着“新朝灵脉图”,图上标注着全国灵脉的分布,每个灵脉节点旁都写着“献祭吉日”——原来王莽早已计划用全国修士的精血祭祀灵脉,妄图突破化神期。刘秀将锦册扔在地上,用脚踩碎:“此等邪术,留之何用。”
城中的百姓和修士听说大捷,纷纷涌上街头,捧着灵米和水迎接汉军。一位白老修士颤巍巍地走到刘秀面前,献上一块“启灵院”的木牌——这是当年卫鞅在咸阳建立启灵院时的遗物,老修士的祖父曾是启灵院的弟子,木牌上“为凡童开掘灵窍”的字迹已模糊不清,却仍能感受到残留的灵气。
“将军,王莽在长安还在搜刮灵脉,不少凡童被抓去填灵脉井。”老修士泣声道,“您一定要救救天下修士啊!”刘秀接过木牌,木牌与手中的残片产生共鸣,他郑重地对老修士说:“老伯放心,我刘秀向天地立誓,若能复汉室,必重开启灵院,让凡童皆可开窍,让灵田归于耕者,绝不让王莽的暴政再现!”
话音刚落,龙睛山突然传来一阵轰鸣,九环锁灵阵的阵纹再次亮起,这次亮起的不是金光,而是柔和的绿光。绿光顺着地脉流淌,所过之处,被九婴焚毁的灵田重新长出灵谷,被蚀灵砂污染的井水变得清澈甘甜,甚至连城中受伤的修士,灵气都在绿光的滋养下缓慢恢复。
“是上古灵脉在自我修复!”刘秀惊喜地现,残片上的纹路与灵脉流动的轨迹完全吻合,“秦法锁灵阵的本意不是镇压,是守护!王莽用错了它,如今才是它真正的样子。”他让士兵在龙睛山周围设立祭坛,供奉秦权和残片,让灵脉的绿光能持续滋养昆阳。
三日后,昆阳大捷的消息传遍天下。绿林军在南阳得知消息,士气大振,立刻向长安进军;赤眉军在樊崇的带领下横扫洛阳,王莽派驻的周礼修士纷纷倒戈;连西域的郑吉旧部都斩杀了新朝校尉,派使者向刘秀表示归附。天下修士终于看到了希望,那些被王莽贬为“徒役”的秦法后裔,纷纷带着祖传的法器和符文赶来投奔,刘秀的军队如滚雪球般壮大。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刘秀在昆阳休整期间,开始着手恢复秩序。他废除了王莽的“井田制”,将没收的公田按“军功丹道”的原则分给士兵和百姓;重开昆阳的启灵院,用龙睛山的灵脉灵气为凡童开窍,老修士的孙子——一个灵根闭塞的少年,在灵脉绿光的滋养下,竟成功开掘了灵窍,成为启灵院的第一个弟子。
他还特意召见了昆阳的儒士和道士,与他们共论法统。儒士桓谭提出“以德化人”,建议减轻刑罚;道士严光主张“道法自然”,建议顺其自然开灵脉。刘秀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说道:“秦法过严,王莽过迂,未来的法统,当取法秦之公正、儒之仁德、道之自然,三者并存,方为长久之计。”这番话让儒士和道士都心悦诚服,纷纷表示愿意辅佐刘秀。
就在此时,长安传来消息:王莽见昆阳大败,竟在明堂中举行“血祭”,用数千名凡童的精血催动“昆仑镜”,妄图引西域的蚀灵沙淹没中原。但他的邪术引了天怒,长安上空出现血雨,百姓和修士动叛乱,攻破了宫门。王莽穿着绣满青鸟纹的礼服,被乱兵杀死在渐台,头颅被割下,传送各地示众。
当王莽的头颅传到昆阳时,刘秀没有像众人那样欢呼,而是对着头颅沉默良久。他想起王莽也曾是饱读诗书的儒士,想起他最初改革时的理想,最终却被权力和邪术吞噬。“法统若失其本心,再完美的制度也会变成暴政。”刘秀对身边的将领说,“我们复汉,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让修士有灵田可耕,让凡童有灵窍可开,让法、儒、道三家各展所长,这才是真正的中兴。”
他将幽冥战甲残片和秦权郑重地供奉在昆阳的启灵院,残片上的血誓纹路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柔和的金光——白起的残魂终于得到安息,秦法的煞气与灵脉的绿光融为一体。刘秀知道,昆阳之战不仅终结了王莽的新朝,更开启了一个新的法统时代,而他肩上的担子,才刚刚开始。
六、中兴之始
昆阳之战结束后,刘秀率军向洛阳进军,沿途的郡县望风而降。百姓和修士们听说刘秀能引灵脉之力、重开启灵院,纷纷带着灵田账簿和法器前来归附,队伍中不仅有秦法修士的后裔,还有儒家的经生、道家的方士,他们虽信仰不同,却都对王莽的暴政深恶痛绝,对刘秀的“三法并存”理念充满期待。
在洛阳城外,刘秀遇到了赤眉军领樊崇。樊崇的赤眉军仍保留着用朱砂染眉的习俗,见到刘秀,他翻身下马,将缴获的王莽“周鼎纹”玉印献上:“文叔,赤眉军愿听你号令,共复汉室。”刘秀接过玉印,玉印上的饕餮纹已失去光泽,他将玉印还给樊崇:“印绶不重要,重要的是天下修士的心。你我约定,未来的灵田分配,按军功,也按德行,儒士教化百姓有功者,道士守护灵脉有功者,都该有封赏。”
樊崇被刘秀的诚意打动,当即表示愿意合并军队。两支起义军在洛阳城外举行了盛大的会师仪式,汉军的玄甲与赤眉军的红衣相映成趣,秦法的雷火符与赤眉的朱砂咒在空气中共鸣,形成一道奇特的灵气屏障,连天空的飞鸟都被这和谐的灵气吸引,盘旋不去。
进入洛阳后,刘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复被王莽破坏的“太学”。太学的旧址上,王莽曾焚毁秦法典籍,如今刘秀命人清理废墟,在原址重建校舍,并亲自题写匾额“三法同辉”。他规定太学中不仅要教授儒家经典,还要设立“律学馆”传授秦法,设立“玄学馆”传授道家术法,让不同信仰的修士都能在这里学习交流。
他还召见了洛阳的灵田主和修士代表,颁布了新的“灵田令”:“灵田归耕者所有,修士按等级缴纳‘灵税’,税银用于启灵院和灵脉维护;禁止私藏蚀灵砂、饕餮鼎等邪器,违者按秦法处置;凡现新灵脉,需上报官府,由官府组织开,不得私占。”这道命令兼顾了公平与秩序,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一天,刘秀在太学巡查时,看到一群儒士、法士、道士正在争论。儒士认为“以德治国”才能长久,法士坚持“以法治国”才能稳定,道士主张“无为而治”才能顺应天道。刘秀没有打断他们,而是指着窗外被灵脉绿光滋养的灵田说:“你们看,灵田要丰收,既需要阳光(儒),也需要雨露(法),还需要土壤(道),缺一不可。法统也是如此,偏执一端则生乱,三者并存方能长久。”
众人听后恍然大悟,纷纷向刘秀行礼。刘秀笑着说:“以后太学要多举办这样的论道,让不同的学说相互借鉴,这才是真正的中兴。”他的目光落在太学角落的一块石碑上,石碑上刻着从昆阳带来的九环锁灵阵残纹,残纹旁新刻了儒家的“仁”字、道家的“道”字,三道纹路相互缠绕,在阳光下泛着和谐的光芒。
就在此时,邓晨从南阳赶来,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王莽的残余势力已被肃清,长安的明堂被改为“灵脉博物馆”,展出从秦到汉的法器和符文,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刘秀在昆阳用过的幽冥战甲残片和秦权,旁边的说明写道:“秦法护灵,汉德承之,三者并存,天下永宁。”
刘秀望着窗外的阳光,心中充满了感慨。昆阳的陨石雨仿佛还在眼前,那些牺牲的士兵、那些重获自由的冤魂、那些在灵脉绿光中重生的灵田,都在告诉他:法统的真谛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顺应民心,守护灵气,让每个修士都有修炼的机会,让每个凡童都有开窍的可能。
他知道,光武中兴的路还很长,但昆阳之战已经为这条路奠定了基石。未来的东汉,将不再是单一的法统,而是法、儒、道三家共生共荣的多元时代,就像昆阳地下的灵脉,既有秦法的坚韧,又有儒道的柔和,在这片土地上,滋养出真正的盛世。
喜欢金戈玄秦请大家收藏:dududu金戈玄秦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