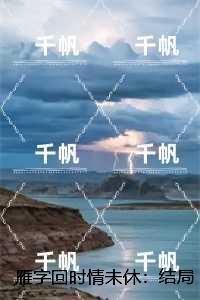紫夜小说>破帷的意思 > 第189章 他们开始用沉默还击(第2页)
第189章 他们开始用沉默还击(第2页)
指尖抚过石案上的竹简——《默问篇》的墨迹还未干透,“问者不须求答,答者不必应问”几个字,在风里泛着青,像刚淬过寒水的刃。
“先生,该开课了。”小书童捧着竹简过来,顶的小辫被风撩起,“孩子们都等在溪边。”
林昭然扶着石案起身,溪水溅起的水珠落在竹简上,晕开个浅淡的圆。
她望着对岸蹲成一排的孩童——有的攥着昨日投进传声井的纸团,有的摸着学堂墙根新砌的砖,目光像溪水般清亮。
风掠过溪面,卷着远处传来的童谣。
那声音很轻,却像种子落进泥里,在静默的土地下,滋滋地着芽。
夜深,小姑娘蜷在草席上,手指抠着嘴角——那里已被石子磨破。
她听见隔壁母亲低声啜泣:“别问了,娘怕你再也说不出话……”她咬紧牙关,把泪水咽回去,只在梦里反复念着那个字:“问……问……问……”
第一日午后,有个扎双髻的小姑娘突然跳起来,石子“啪”地掉在地上。
“我要说!”她的声音带着童稚的尖锐,惊得溪边的白鹭扑棱棱飞起,翅膀拍打空气的声响划破寂静。
林昭然接住她摔过来的石子,指腹触到石上还带着小姑娘的体温,微潮而温热。
她蹲下来与那孩子平视,看见她眼眶里转着的泪,像两粒要坠未坠的星子。
“你恨我说不出话?”她用拇指抹掉孩子脸上的泪,“可阿梨姐姐去年在晒谷场问‘十年后呢’,问了七遍,没人答;老周头在传声井问‘为何官仓满而民饥’,投了十八张纸,没人答。他们说了,却没人听——这样的说话,比哑了更痛。”
小姑娘的泪珠子“吧嗒”掉在她手背上,温热的,林昭然轻轻替她把石子重新塞回舌下:“你试着用眼睛问,用手指问,用你跺脚的力气问。等你问得连风都绕着你转,连云都停在你头顶,那时石子自己会从嘴里滚出来。”
第二日傍晚,阿木突然扯了扯她的衣袖。
他举着两根草茎,一根折成半寸,一根留作原样,然后用眼睛盯着她——这是前日她教他们用草茎算田亩时的法子。
林昭然笑了,屈指在他手心里画了个“二”字。
阿木的眼睛倏地亮起来,又慌忙抿住嘴,把草茎郑重塞进她手里。
第三日清晨,晨雾未散时,林昭然踩着露水走到溪边。
十五个孩童整整齐齐跪坐在青石板上,舌下的石子泛着湿润的光,像含着未化的霜。
阿梨妹妹歪着脑袋,用食指在泥地上画了个歪扭的“问”字;扎双髻的小姑娘把草茎编成小辫,举到她面前晃了晃——那是她昨日说“阿娘的头比绸缎还软”时的模样。
最边上的阿木突然抬头,目光像淬了晨露的竹尖,直直刺进她心里。
“这才叫学会说话。”林昭然的声音轻得像雾,却在晨风中散得很远。
她伸手抚过阿木的顶,指腹触到他后颈薄汗的温度,微黏,带着生命的热度。
“你们看,舌头被捆住时,眼睛会替它走万里路;喉咙被堵住时,指尖会替它写千行字。”
远处传来竹哨声,是柳明漪的联络信号。
林昭然扶着石案起身,腰腹的旧伤咯地一响,她却像没知觉似的,望着孩子们跟着小书童去溪边洗手的背影,袖中攥着的《默问篇》竹简硌得掌心生疼。
“明日开始教《目述》。”她对自己说,声音轻得只有风听见,“要教他们用睫毛的颤问,用肩膀的沉问,用脚底板的温度问——问到那些堵嘴的人,夜里睡觉都要被这些问硌醒。”
第五日黄昏,乌云压境。
林昭然站在“敬天席”中央,粗麻衫被雨水浸得透湿,贴在身上像块冰凉的膏药,寒意渗入骨髓。
她将陶碗高举过头时,腕骨咯地一响——那是三个月前咳断的肋骨留下的旧伤。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她望着周围百来个百姓——有织户,有盐工,有老秀才,还有阿梨妹妹举着的陶碗里,盛着半碗雨水。
“他们怕的不是我们说什么。”她的声音混着雨声,却清晰得像击磬,“是我们不再需要他们批准说话。”
话音未落,她端起自己的陶碗,将雨水缓缓倾倒在泥地上。
水流蜿蜒着,竟真的汇成个“问”字,笔画粗重如刀刻。
可新雨来得急,不过三息,那个“问”字便被冲散,只余下几滩浑浊的水洼。
人群里传来抽气声。
程知微站在竹篱外,望着雨幕中模糊的人影,忽然想起前日在县学外,百姓离开时鞋跟撞地的整齐声响——那不是沉默,是千万颗心在敲鼓。
他摸了摸腰间的盐囊,突然觉得掌心烫,像是攥着把正在融化的冰刃。
而此刻的承明殿里,沈砚之执起狼毫,在《贞观政要》“水能载舟”旁添了行小字:“亦能淹殿。”墨迹未干,他的指节便重重抵在案上,砚台里的墨汁溅出来,在“淹殿”二字上晕开团黑雾,像极了今夜京畿方向的天空。
翌晨,天光初透。
柳明漪蹲在传声井边,指尖抚过井壁新刻的“问”字。
她望着远处学堂墙根的新砖,忽然听见田埂上传来响动——几个农夫正用泥抹子修补被雨水冲垮的田垄,泥抹子起起落落间,她瞥见田埂上歪歪扭扭的痕迹,像极了被雨水冲散的“问”字。
“字不必在路……”她喃喃自语,泥抹子的“啪啪”声里,忽然有粒泥点溅在她手背上,烫得她猛地缩手。
那泥点里混着半片烧过的纸灰,在晨光里泛着淡金——是传声井焚纸时落进泥里的。
柳明漪望着田埂上忙碌的农夫,忽然笑了。
她转身往织坊走,裙角沾着的泥点在青石板上留下一串浅痕,像一行没写完的字。
喜欢破帷请大家收藏:dududu破帷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