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夜小说>重生赌徒 > 第159章 微弱的曙光(第1页)
第159章 微弱的曙光(第1页)
自那次咖啡馆不欢而散的会面后,林少莲并未放弃。
她深知,对于何志明这样深陷自我否定泥潭的人,一次的挫败微不足道,持续的、不带压力的关注,或许才是唯一可能渗透坚冰的方式。
她没有再主动打电话或邀约,那只会激起他更强烈的抗拒。
她选择了更迂回,也更温和的方式。
她通过一位与何家相熟、且不知内情的老朋友,辗转了解到何志明偶尔会在深夜小区无人时,出来漫无目的地散步。
于是,她开始“偶然”地在那个时间段,出现在那个小区附近。
第一次“偶遇”时,何志明看到她,像是受惊的兔子,猛地顿住脚步,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和难以置信,随即几乎是立刻转身,快步消失在了夜色里。
林少莲没有追赶,也没有呼喊,只是站在原地,如同什么都没有生。
第二次,第三次……她依旧只是出现,有时是刚从附近的书店出来,手里拿着几本书;
有时像是刚结束散步,与他擦肩而过时,会极其自然、轻微地点一下头,如同对待一个不太熟的邻居,然后便继续前行,绝不驻足,绝不多言。
这种沉默的、不带评判的“在场”,渐渐削弱了何志明最初的尖锐抗拒。
他不再像第一次那样仓皇逃窜,虽然依旧会立刻移开视线,加快脚步,但那种如临大敌的紧张感,在慢慢减退。
终于,在第五次还是第六次“偶遇”时,当林少莲如同往常一样与他擦肩,即将走过时,身后传来一个极低、极沙哑的声音:
“……你何必。”
林少莲停下脚步,转过身。
月光下,何志明站在几步开外,没有看她,低着头,身影在路灯下拉得细长而孤单。
“我只是刚好路过。”
林少莲语气平静,听不出任何刻意。
何志明出一声极轻的嗤笑,显然并不相信,但他没有戳破,也没有离开。
这是一种默许,默许了她的“存在”。
这是一个微小的,却是至关重要的突破。
自那晚之后,他们的“偶遇”开始有了极其简短、近乎吝啬的交流。
“天气冷了。”
“嗯。”
“这本书还不错。”林少莲扬起手中的书。
“……哦。”
对话内容空洞无物,但重要的是,交流本身在生。
何志明开始允许她存在于他封闭世界的边缘,哪怕只是最外围。
林少莲极富耐心,她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条刚刚建立的、脆弱的沟通纽带,从不逾越。
她不再提工作、未来、过去这些沉重的话题,只是聊最无关痛痒的日常,像对待一个需要重新学习如何与外界建立连接的病人。
转机生在一个飘着细雨的夜晚。
林少莲撑着伞,看到何志明独自站在小区花园的凉亭里,望着雨幕出神,身上已经被飘进的雨丝打湿了些许。
她走过去,将伞稍稍向他那边倾斜。
何志明身体僵了一下,但没有躲开。
两人沉默地站了一会儿,只有雨声淅沥。
“我爸妈……在托关系,想给我找个闲职。”
何志明忽然开口,声音在雨声中显得有些模糊,带着一种认命般的疲惫。
“他们觉得,我总得有点事做,像个‘正常人’。”
林少莲心中一动,这是一个信号,一个他内心或许也在挣扎着想要“正常”起来的信号。
“你怎么想?”她轻声问。
“我不知道……”何志明摇了摇头,语气里充满了茫然和无所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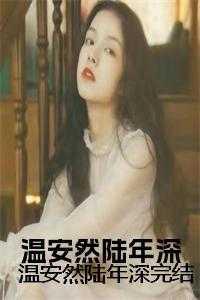
![肝帝无所不能[全息]+番外](/img/2339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