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夜小说>心在跳视频播放 > 已经不一样了(第1页)
已经不一样了(第1页)
已经不一样了
时间在卑尔根黏稠湿润的空气里,仿佛被拉长了,又仿佛被加速了。窗外的雨依旧遵循着它自己的节奏,时而细密如雾,时而瓢泼如注,周而复始。当我某天清晨站在镜前,注意到镜中人似乎比记忆中抽高了些许,眉宇间那份挥之不去的惊惶被一层更深的丶沉静的疲惫覆盖时,才惊觉,日历已经悄无声息地翻过了一年。
我,季知秋,在卑尔根,已经成为了一名高三学生。
这一年,像一场漫长而缓慢的物理治疗。汉森医生诊室里那盆绿植似乎更加茂盛了些,而我,不敢说痊愈,但至少,学会了与内心的野兽共存。那片白色的小药片依旧是我每日的功课,只是剂量在汉森医生的监控下,经过了数次精细的调整。恐慌发作的次数减少了,强度也减弱了。它们不再像突如其来的海啸,能将我瞬间卷入灭顶之灾,更像是不期而至的退潮,留下湿冷和不适,但我已能记得运用那些技巧——命名五样东西,感受脚踏实地的重力,深呼吸——让自己在退潮中站稳,等待它过去。
学业是另一重锚点,或者说,是我为自己构筑的堡垒。高三的氛围在全球似乎都是共通的,紧张感如同卑尔根冬季提前降临的夜色,无声地渗透进每一寸空气。课表排得更满,作业和项目研究占据了大量的课馀时间。北欧的教育体系并非只有宽松,到了关键时刻,竞争的暗流同样涌动。
令我自己也有些意外的是,我的成绩,竟稳定在了年级前十。
这并非轻而易举。语言的壁垒依然存在,尽管艾拉丶利维亚他们不遗馀力地帮助我,尽管我的挪威语已经从一片空白进步到能进行日常交流和理解大部分课堂内容,但在涉及专业术语和深度论述时,我仍需付出比本地学生多几倍的努力。无数个深夜,当窗外的雨声成为唯一的伴奏,我独自在台灯下,对着艰涩的课本和论文资料,逐字逐句地啃噬。疲惫和困倦如同湿透的棉被压下来时,我便会在心里默念那三个短句,像念诵咒文。
“要考上好大学。”
“变得更好。”
“然後,回去找他。”
程砚初。是这片异国阴霾天空下,唯一清晰闪烁的北极星。他的照片依旧立在我的书桌一角,一年了,我们没有通过一次电话,没有发过一条信息。距离和时差像一道天然的屏障,也像是我自我设定的考验。我害怕听到他的声音会瓦解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平静,更害怕从他口中听到任何关于他新生活的丶与我无关的消息。沉默,成了我维系这份情感的丶笨拙而唯一的方式。
但他在我的生活里,无处不在。
我的数学笔记整理得一丝不茍,因为他曾说过喜欢逻辑清晰;我强迫自己参加小组讨论,尽管开口前心脏依旧会紧缩,因为他不会希望我永远躲在角落;我甚至开始尝试慢跑,在弗洛伊恩山脚下的小径上,想象着他如果在身边,会以怎样稳定配速沉默地陪跑。他成了我衡量自己进步的一把隐形的尺子,每一个好成绩,每一次在课堂上鼓起勇气的发言,每一次没有在抑郁情绪中彻底沉沦,都让我觉得,离他近了一点点。
而学校,这片曾经让我感到无比疏离的土地,在过去的一年里,竟渐渐染上了温暖的色彩。
利维亚丶艾拉丶索菲亚和马库斯,我们的小团体稳固如山。高三的紧张并没有驱散我们的友谊,反而因为共同面对学业压力而更加紧密。课间休息的十分钟,依旧是我们雷打不动的欢乐时光。
“知秋!快看,这是我昨晚熬夜画的物理电路图,像不像一幅抽象派杰作?”利维亚顶着一头似乎永远充满活力的红发,把笔记本拍在我面前,上面的线条蜿蜒扭曲,颇具後现代风格。她早已放弃用我基本听不懂的快速挪威语轰炸我,转而使用一种混合了夸张肢体语言和简单词汇的“利维亚式”沟通。
艾拉则会在一旁笑着摇头,用流利的英语精准地替我翻译利维亚的“狂想”,并补充上正确的知识点。“别听她的,知秋,这是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混淆的典型错误案例。给,这是我的笔记,重点都标出来了。”
索菲亚的赞美则升级了。“哦!季知秋!你今天解题时微微皱眉的样子,充满了智慧的吸引力!我敢打赌,奥利维亚老师(数学老师)都被你迷住了!”她的直白依旧让我耳根发热,但我不再只是讷讷地道谢,偶尔会回以一个极浅的丶无奈的微笑。这总能引发她更大的热情。
马库斯依旧沉默,但他的行动力更强了。他会默默地把从家里带来的丶他母亲烤的北欧风味肉桂卷分给我,会在小组项目分工时,主动承担需要大量对外沟通的部分,把我安排在需要专注和细心的资料整理和分析环节。他的体贴是一种无声的背景音,让人安心。
我们依旧一起午餐,一起在图书馆奋战,周末的聚会也成了固定的减压方式。那场大雨中的篝火晚会,我最终去了。在海边,巨大的篝火堆燃烧着,驱散了雨夜的湿寒。利维亚和索菲亚真的拉着我,笨拙地跳起了挪威的传统舞蹈,脚步杂乱,笑声却响彻海滩。马库斯在一旁用吉他弹着简单的和弦,艾拉跟着哼唱。那一刻,火光映在每个人年轻而欢快的脸上,海风裹挟着木柴燃烧的噼啪声和咸腥的气息吹过,我站在他们中间,虽然动作依旧生涩,心情依旧带着一层隔膜,但那份“不确定的期待”变成了真实的丶微小的快乐。我确实触碰到了那团篝火,感受到了它的温度。
这一年,卑尔根于我,不再仅仅是一张冰冷的明信片。我熟悉了鱼市里每个摊位老板的大致模样,知道了哪条小巷的咖啡馆有最醇厚的热巧克力,爬了无数次弗洛伊恩山,见证了它春夏的葱郁,秋季的火红,和冬季覆上一层薄雪时的静谧。这座城市的美,带着雨水的浸润和峡湾的深沉,缓慢地丶固执地渗入了我的生命。
然而,欢快氛围的烘托下,是我内心从未停止的丶对八千多公里外的回响。这种回响,在一年後的某个平凡夜晚,迎来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
那是一个典型的卑尔根秋夜,雨下得不大,但绵绵不绝。我刚结束一个小组视频会议,和利维亚他们讨论完一个复杂的生物项目。窗外一片漆黑,只有路灯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反射出昏黄的光晕。我感到一种深沉的疲惫,不仅是学业上的,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孤寂。尽管白天在学校被朋友们的欢声笑语包围,但回到这间寂静的公寓,那种熟悉的丶与世界隔着一层玻璃的感觉又会悄然回归。
我习惯性地点开了那个几乎已经成为我肌肉记忆的页面——程砚初所在高中的校园论坛。这是我一年来唯一的“越界”行为,是我窥探他生活的一扇微小窗口。我知道这有些病态,但这能让我感觉到,他依旧在一个我可知的丶未改变的世界里生活着。
论坛大多是关于竞赛丶考试和校园活动的枯燥信息。我通常只是快速地浏览标题,寻找任何可能与他相关的蛛丝马迹,比如数学竞赛获奖名单,或是物理小组活动通知。大多数时候一无所获,但这个过程本身,就带有一种隐秘的慰藉。
就在这时,一条不起眼的丶发布于数小时前的新帖子标题,像一根冰冷的针,猝不及防地刺入了我的视线——
【讨论】高三摸底考排名出炉!程砚初稳坐年级第一,甩开第二十分!学神的世界我不懂!】
我的心跳骤然停了一拍,随即失控般地狂跳起来,撞击着胸腔,带来一阵熟悉的闷痛。手指有些颤抖地点开了帖子。
主楼是冰冷的成绩列表截图,在密密麻麻的名字和分数中,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刻在心底的名字,高悬榜首,各科成绩近乎完美。下面已经有了几十条回复。
“程神还是程神,给条活路吧!”
“听说他最近在准备一个全国性的物理竞赛,目标是保送Q大。”
“感觉程砚初比以前更冷了,上次问他题,就回了三个字‘看教材’,惜字如金啊。”
“楼上+1,感觉他眼里只有学习,没什麽能让他动容的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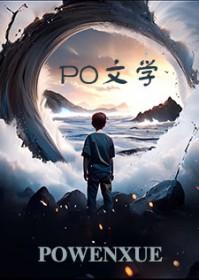
![绝地科学家[综英美]](/img/22197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