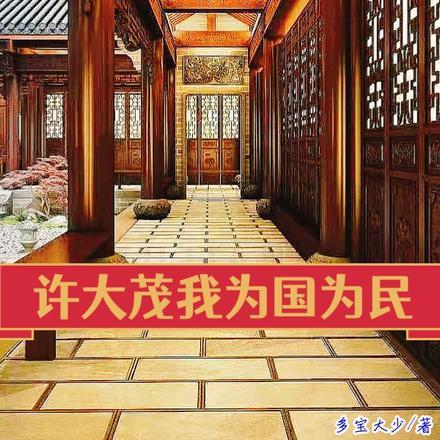紫夜小说>万里江山一梦还是一梦 > 明媚谁人不看来(第2页)
明媚谁人不看来(第2页)
北秦一向是最崇尚英雄的地界,在口舌咀嚼他的桃色故事,也算是一种隐隐的宣泄。
卖花女在将军府後门与洗衣妇窃窃私语,绸缎庄的夥计打包货物时,不忘往箱笼里塞几句秘闻,连寺庙里的香客都在菩萨面前嘀咕这事。
说那忠烈遗孀的孤女吕盈,眉眼间竟有几分淳于氏的风骨,提起二十年前某个雨夜,有人见大将军孤身策马入寡妇宅院,直至天明方归。
话头越传越真,渐渐连军中老卒都开始侧目。
黎梦还坐在王府後院的石亭里,指尖轻叩案几。
亭外一株初桃尚未开花,枯枝横斜,映在青灰色的天幕上,像一道未愈的疤。
她听着探子回报,唇角微勾,眼底却无笑意。
淳于坚正在校场操练新兵,听说黎梦还到来,他擦把汗匆匆赶到:“阿梦怎麽来了?”
“路过看看。”黎梦还递上汗巾,“听说氐王近日身体欠安?”
淳于坚神色一黯:“父亲夜不能寐,太医说是心火旺盛。”他压低声音,“城里那些流言,你也听说了?”
黎梦还故作惊讶状:“什麽流言?”
淳于坚犹豫片刻,终究摇头:“没什麽。无要事,还是少来王府为好。近日不消停。我有空再去寻你可好?”
刚入春的雍州城飘着柳絮,风里带着未央宫新漆的桐油味。黎梦还倚在朱雀阙的望楼上,看那些柳絮粘在戍卫的玄甲上,像给铁衣缀了层不合时宜的轻雪。
不远处,近来总爱站在城楼上的淳于雄正在远眺。
他身形依旧挺拔,铠甲未卸,可鬓边霜色已深,眼底锐气也被岁月蚀去了棱角。
风掠过旌旗,猎猎作响,他伸手按住腰间佩刀,却摸到刀鞘上一道旧痕。
是当年与义弟并肩杀敌时留下的。
“银甲郎,金刀客,旧年桑枝栖双雀。”
“双雀飞,巢空悬,谁家新燕啄故檐?”
淳于雄第一次见到章明月,是在义弟的灵堂前。
烛火摇曳,她一身素缟跪在棺前,背影瘦削如刀。
淳于雄上前扶她,掌心触及她冰凉的手腕时,她的眼底只有一片死寂的平静。
後来,她成了他帐中的常客。
夜半烛影里,她总爱抚着微微隆起的小腹,轻声问:“这孩子……该姓什麽?”
如今,这秘密终于被黎梦还翻了出来,晾晒在雍州的阳光下。
春寒未褪,雍州城内的积雪却已开始消融。
街巷间的泥泞里混杂着碎冰,行人踏过时溅起的水花沾湿袍角,像是某种无声的侵蚀。
黎梦还送别见淳于雄,是在他搬往祖地别院前,雍州的一切交托给了淳于坚,而他只着一袭灰袍,像她在现代遇到过的普通退休老干部。
他深深地凝视着面前的女子,神色却不那麽地桀骜,反而露出一点棋逢对手的兴趣。
屏退左右後,他长叹一声道,“你很有本事,能够谋算我到这一步。无论你是为了南梁丶东燕还是宇文氏,有你在,北秦再也光复不了我父亲的荣光了。”
黎梦还微微一笑,“就算是到现在,氐王您还是小瞧了我。但是你也小瞧了坚头,你要保重身体,他会让淳于氏的功绩有胜过他祖父的那一天。”
淳于雄神色一滞,端详着黎梦还真诚的神色,轻叹一声道,“那我也只能宁可信其有。人都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负责,如今撤手,能免得最後的不堪,想来也是你的留情,没有让我们淳于氏一族终结在内斗之中。我膝下的孩子都是赤子之心,你和穆昭不要轻易糟蹋去了。我这一生为国为家,有过太多後悔之事,想要握住全局,却最终只是一盘散沙。”
黎梦还静立片刻,轻声道:“你最後悔的事情,我永远不会叫坚头知道。”
淳于雄的腰背依旧挺直,可马匹的步伐却比往日迟缓。行至护城河畔时,他忽然勒马,回头望了一眼都城,这一眼,像是在看自己的一生。
风掠过城墙,卷起几片残雪。黎梦还拢了拢衣袖,带着神情复杂的淳于坚转身离去。
她知道,从今日起,淳于雄再也不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