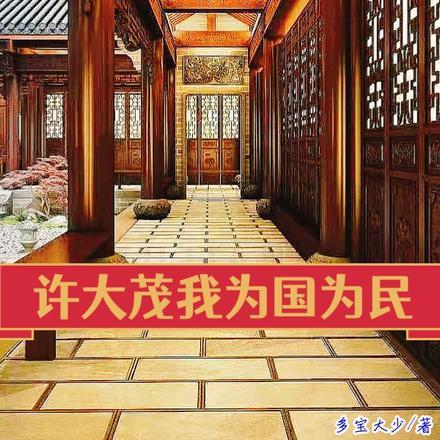紫夜小说>万里江山一梦还是一梦 > 短丛香玉映清湍(第1页)
短丛香玉映清湍(第1页)
短丛香玉映清湍
“南梁自顾不暇。”颍川陈氏的家主陈邕,须发花白,眼神却锐利如鹰隼。
他是这些豪强中实力最雄厚的,也是心思最深沉的。他拈着胡须,声音低沉,“扬州,皇帝沉迷丹鼎,权臣争权夺利,谁还顾得上这淮北苦寒之地?求援不过是自取其辱!”
“那怎麽办?坐以待毙吗?”一个年轻些的家主声音发颤,“冀州那位的手段,诸位不是没听过!人头落地,三族尽诛!我们……”
“慌什麽!”一直沉默的许昌司马氏家主司马徽,终于开口。他年约四十,面容清癯,带着世家子弟特有的矜持与傲慢,但眼底深处也藏着挥之不去的忧虑。
“黎女再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冀州新定,她哪来的馀力立刻南下?无非是虚张声势!我们各家坞堡坚固,粮草充足,只要联起手来……”
“联手?”陈邕冷笑一声,打断了他的话,目光锐利地扫过在场诸人,“司马兄说得轻巧。联起手来,谁来当盟主?谁来指挥?是听你许昌司马氏的,还是听我颍川陈氏的?又或者,听这位孙老弟的?”他毫不客气地点破了各怀鬼胎的现实。
“况且,联起手来做什麽?真跟北军硬拼?别忘了,雍州淳于坚的玄甲军,那可是踏平东燕王帐的虎狼之师!我们这坞堡私兵,守守家丶欺压欺压佃户还行,对上正规军阵?”
他这番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衆人头上。
联合作战?谈何容易!各家积怨已久,为水源丶为田界丶为商路,明争暗斗从未停歇。谁肯服谁?谁又敢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到别人手上?
“那……陈公的意思是?”孙茂小心翼翼地问。
陈邕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茶盏,慢悠悠地呷了一口。目光却越过厅堂敞开的窗户,投向坞堡外广阔的田野。
那里有陈家的佃农正佝偻着背,在刚刚解冻的土地上艰难翻动,面黄肌瘦,眼神麻木。
他又想起了前些日子,那个冀州来的“粮商”百里融,带着玩世不恭的笑容,却说着最诛心的话:“陈公,坞堡再高,能挡住饿疯了的流民吗?粮仓再满,能填饱几万张嗷嗷待哺的嘴?北边的黎帅说了,地,只要肯开荒,三年内就是自己的。粮,只要肯种,只收三成租。您这坞堡里存粮再多,能存几年?能挡得住人心所向?”
人心……陈邕心中猛地一抽。他当然知道自家坞堡之外是什麽景象。饿殍不是没有,只是被家丁远远地丢到了乱葬岗。
佃农的抗争越来越频繁,虽然被强力镇压下去,但那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
黎梦还的《劝农令》和减租政策,就像野火,随着流民和那些行医施药的医官们,早已在豫州底层悄然蔓延。他陈家能压得住一时,压得住这燎原之势吗?
“黎梦还派人来了。”陈邕放下茶盏,声音不高,却让整个大厅瞬间死寂。“不是大军,是使者。带来了她的亲笔信。”他从袖中取出一封火漆封口的信函。
衆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其上,带着惊疑和恐惧。
“信里怎麽说?”司马徽的声音有些发紧。
陈邕展开信笺,目光扫过上面铁画银鈎的字迹,“其一,承认豫州现状,各郡县可维持自治,但须遵《北律》基本纲纪,不得私设刑狱,不得苛虐百姓。其二,开通商路,冀州盐铁丶豫州粮秣,公平互市。其三,”他的目光扫过衆人,“献地归附者,按献地多寡及治理之功,授五等爵田。开国男爵,献地万亩以上,享封邑,减徭役五年。”
“五等爵田?”孙茂眼睛一亮,爵位和封邑,这是他们地方豪强梦寐以求的朝廷认可!虽然爵位名称古怪,但实打实的封邑和减役是看得见的实惠!
“哼,诱饵罢了!”司马徽脸色难看,“这是要我们自断根基!献地?没了土地,我们还算什麽豪强?!”
“根基?”陈邕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司马兄,你的根基,是这坞堡高墙,还是外面那些恨不得生啖你肉的佃户?又或者是南梁那遥不可及的丶早已抛弃我们的朝廷?”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指着远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的一片烟尘,“看看那边是什麽!”
衆人纷纷挤到窗边望去。只见远处开阔的平原上,一支沉默的黑色洪流正在集结。
玄色重甲在初春的阳光下反射着冰冷的光泽,阵列森严,长槊如林,巨大的陌刀方阵如同移动的钢铁丛林,每一次整齐的顿地,都仿佛让大地微微震颤。
一面巨大的玄色“黎”字大纛,在风中猎猎招展,带着睥睨天下的威势。没有鼓噪,没有挑衅,只有那如山如岳丶沉默无言的压迫感,隔着数里之遥,都让人心胆俱寒。
是威名赫赫的征虏将军元登!他们在演练!在耀武!
一股冰冷的寒气瞬间从衆人的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所有的侥幸,所有的傲慢,在这绝对的力量展示面前,被碾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