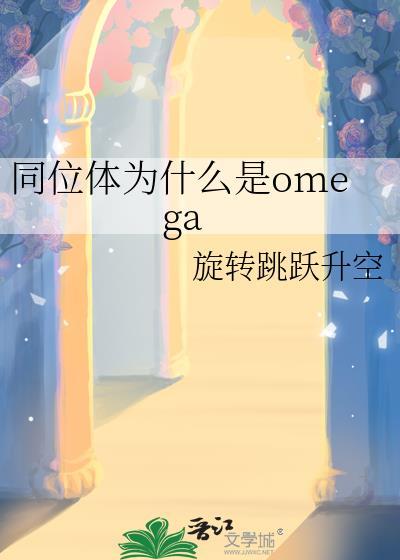紫夜小说>承爵 > 第64章(第1页)
第64章(第1页)
他像一台被重新编程的机器,缓慢而稳定地运行着,规避着所有可能引发系统崩溃的风险。
画廊那边,他彻底放了手,只保留了最大股东的身份,不再参与任何具体运营。副手偶尔会打电话来请示一些重大决策,他听着,给出最理性、最符合商业逻辑的意见,语气平淡得像在讨论别人的生意。
他开始尝试接触一些全新的东西。报名了一个陶艺班,手指触摸湿润黏土的触感,带着一种原始而踏实的反馈。还买了几本园艺书,在阳台上摆弄几盆绿萝和薄荷,观察它们抽枝长叶的过程,缓慢,安静,不reire任何回应。
生活像一潭被投入了明矾的死水,渐渐沉淀,变得清晰,却也失去了所有波澜。
直到有一天,他在陶艺班完成了一个歪歪扭扭、勉强能看出是杯子的作品。老师笑着鼓励他,说很有“侘寂”之美。旁边一个同样来学陶艺、性格开朗的大妈凑过来看,啧啧称赞:“小江手真巧!这杯子留着,以后给你女朋友用正合适!”
这三个字像一根细小的刺,猝不及防地扎进江郁看似已经结痂的心口。
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握着那个粗糙陶杯的手指微微收紧,指节泛白。
周围的声音仿佛瞬间远去,只剩下心脏在空洞胸腔里、一下下沉闷的跳动声。
他没有女朋友。
以后……大概也不会有了。
那个人,把他爱人的能力,连同被爱的资格,一起带走了。
他垂下眼帘,掩去眼底一闪而过的狼狈和痛楚,再抬起头时,脸上已恢复了那种无懈可击的、带着淡淡疏离的平静。
“随便做着玩的。”他轻声说,将那个陶杯放到一旁,转身去清理工作台。
那天之后,他再也没有去过陶艺班。
时间依旧不紧不慢地流淌。秋深了,河边的梧桐树叶落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白色的天空。
江郁的生活依旧保持着那种令人窒息的规律。他看起来“好”了很多。体重恢复了一些,脸色不再那么骇人的苍白,能进行正常的社交(虽然仅限于浅尝辄止的寒暄),甚至能对着江澄偶尔带来的笑话,牵起嘴角露出一个算不上灿烂、但至少不再僵硬的微笑。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内里某个部分,已经永久性地损坏了。
像一件被高超工匠修复的古董瓷器,表面光洁如新,能盛水,能插花,履行着作为容器的基本功能。但敲击时,发出的不再是清越悠扬的回响,而是一种沉闷的、带着细微杂音的钝响。
他不再轻易感到剧烈的痛苦,但也失去了感受深切快乐的能力。情绪被压缩在一个极其狭窄的波段内,大部分时间,是一种无悲无喜的麻木。
他开始能够理智地、甚至带着几分学术性的冷静,去回顾和剖析他与贺凛的那段过往。看清了自己的怯懦、自私和那些隐藏在“骄傲”下的、不堪一击的自卑。也看清了贺凛那份爱里的偏执、笨拙和……或许,从一开始就注定悲剧的、过于沉重的分量。
没有怨恨,没有不甘,只剩下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一种……尘埃落定后的了悟。
他们之间,就像两条短暂交汇又注定分离的轨道,因为巨大的引力而碰撞,迸发出毁灭性的火花,然后,在各自的轨道上,带着满身伤痕,继续奔向无法重叠的远方。
这样……也好。
至少,那个人得到了他想要的“平安顺遂”。
而他自己,也在这片废墟之上,勉强搭建起了一个能够遮风避雨、哪怕冰冷空洞的容身之所。
这天傍晚,江郁像往常一样,在滨河公园散步。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走到固定的长椅前,坐下,看着被落日染成金红色的河面。
一个皮球滚到他的脚边。
他弯腰捡起,一个三四岁大的、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摇摇晃晃地跑过来,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看着他,奶声奶气地说:“谢谢叔叔。”
江郁将球递还给她,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一丝极淡的、真实的柔和:“不客气。”
小女孩抱着球,咯咯笑着跑开了,扑向不远处张开双臂等待她的年轻母亲。
江郁看着那对母女嬉笑的背影,目光有些悠远。
曾经,是否也有过那么一个人,用那样全然信赖和依恋的眼神看过他?是否也曾幻想过,某种……类似于“家”的、温暖而琐碎的future?
心脏传来一阵熟悉的、细微的抽搐。并不剧烈,更像是一种习惯性的、条件反射般的钝痛。
他缓缓收回目光,重新望向波光粼粼的河面。
夕阳正在下沉,最后的余晖像熔化的金子,流淌在水面上,绚烂,却转瞬即逝。
就像某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和某些,再也见不到的人。
他静静地坐着,直到夜幕完全降临,华灯初上,将河岸点缀成一条流光溢彩的丝带。
然后,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被晚风吹得微凉的外套,沿着来时的路,一步一步,沉稳地,走向那个没有人在等待、但至少属于他自己的……“家”。
背影在渐浓的夜色里,显得单薄,却异常挺直。
像一棵在严冬里落光了所有叶子、却依旧顽强扎根于地的树。沉默地,承受着风霜,也沉默地,等待着连自己都不知道是否会到来的……下一个春天。
“哥!有个好消息!
时间像指间沙,在刻意维持的平静中悄然滑落。江郁在新公寓里度过了一个安静到近乎虚无的冬天。规律的作息,简单的饮食,定期的复诊和服药,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他像一件被精心修复的哥窑瓷器,表面的开片纹路被金粉细心填补,光洁如新,能摆上台面供人观赏,内里的裂痕却只有自己知道,每一次轻微的温度变化,都可能引发细微的、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崩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