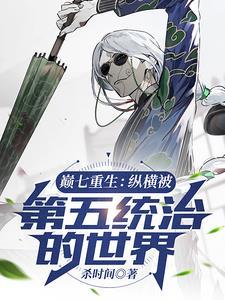紫夜小说>承爵 > 第65章(第1页)
第65章(第1页)
春天来临的时候,河边的柳树抽出嫩绿的新芽,空气里带着万物复苏的潮湿气息。这种生机勃勃,与他内心的沉寂形成了尖锐的对比。他依旧散步,画画,看书,甚至开始尝试翻译一些冷门的艺术理论著作,用繁复的学术语言填塞思维的每一寸空隙,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回忆趁虚而入。
江澄来看他的频率降低了,见他情况稳定,也稍稍放心,开始更多投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她偶尔会带来一些圈内的消息,总是小心翼翼地过滤掉所有可能与“贺”字沾边的内容。
这天,江澄来时,脸上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兴奋。
“哥!有个好消息!”她放下带来的水果,声音雀跃,“你记得‘弥新’艺术基金会吗?就是那个特别难搞、但资源顶级的基金会!”
江郁从一本厚重的德文艺术史中抬起头,眼神有些茫然。“弥新”?他有点印象,一个背景深厚、以扶持具有跨文化视野的当代艺术家和策展人闻名的基金会,门槛极高。
“他们刚刚公布了一个全新的策展人扶持计划,‘破界之声’!”江澄激动地说,“面向全球招募,最终入选者不仅能获得巨额资金支持独立策展,还能得到基金会全方位的资源倾斜,甚至有机会在他们即将落成的、由顶级建筑师设计的新地标美术馆里实现首展!”
江澄看着他依旧平静的脸,强调道:“哥,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以你的资历和眼光,完全可以去试试!这比你窝在家里翻译这些天书有意义多了!”她指了指他面前那本厚厚的德文书。
江郁沉默着。手指无意识地划过书页边缘。“弥新”基金会……他依稀记得,这个基金会的创始家族异常低调,但其在海外,尤其是北欧的资本和艺术资源网络,深不可测。
心里某个角落,似乎被极轻微地触动了一下,泛起一丝难以捕捉的涟漪。但他很快将其压制下去。
“我现在这样,挺好。”他垂下眼帘,声音平淡,“不想再折腾了。”
“这怎么是折腾呢?”江澄急了,“这是你的事业啊!哥,你难道真要一辈子躲在这里吗?那个贺……”
她猛地刹住车,脸色白了白,懊恼地咬住嘴唇。
空气有瞬间的凝滞。
江郁握着书页的手指微微收紧,指节泛出淡淡的白色。他抬起头,看向窗外抽出新芽的柳树,目光没有焦点。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他轻声说,语气里听不出情绪,“但我真的……没那个心力了。”
他厌倦了名利场的倾轧,厌倦了带着面具的周旋,更厌倦了……那种需要投入巨大情感和热情才能做好的事情。他现在的状态,就像一块被抽干了所有水分的海绵,坚硬,脆弱,再也无法柔软地吸收和释放任何东西。
江澄看着他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又气又心疼,最终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然而,有些种子一旦被播下,即便落在看似贫瘠的土壤里,也会悄无声息地寻找萌发的机会。
接下来的几天,“弥新”基金会的“破界之声”计划,像一只无形的手,时不时地撩拨一下江郁死水般的心湖。他强迫自己不去关注,但那些关于计划细节、评审阵容、往届获奖者辉煌履历的新闻,还是会通过各种渠道,零星地闯入他的视野。
他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思考,如果由他来策划这样一个展览,主题会是什么?会选择哪些艺术家?如何构建叙事逻辑?
这些专业性的思考,像久旱土地上降下的微雨,虽然无法立刻滋润干涸的深层土壤,却至少让表层不再那么僵硬。
他开始在散步时,留意河边那些被丢弃的、形态各异的工业零件和自然物;在翻阅艺术书籍时,会对某些关于“边界”、“废墟”、“重生”的论述多看几眼。
一种微弱到几乎无法察觉的、属于“创造”的本能,似乎在冰封的深处,极其缓慢地苏醒。
这天复诊,心理医生陈谨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状态的细微变化。
“最近似乎对某些事情重新产生兴趣了?”陈医生温和地问。
江郁沉默了一下,没有隐瞒,简单提了一下“弥新”基金会的计划。
陈医生点了点头:“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江先生。不必把它看作是一个必须去竞争和证明的战场,或许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与自己对话的练习。尝试去触碰那些你曾经热爱、后来因为痛苦而回避的东西,看看它们现在对你意味着什么。”
与自己对话的练习……
江郁咀嚼着这句话。
晚上,他鬼使神差地打开了许久未用的专业笔记本电脑,登录了“弥新”基金会的官方网站。纯黑底色的页面,设计极简而充满力量感。“破界之声”计划的招募海报在首页滚动,巨大的白色字体冲击着视觉——“于无声处,听惊雷。”
他的心脏莫名地悸动了一下。
他点开了申请入口。需要提交一份详尽的策展方案提纲,个人履历,以及……一封阐述个人理念与项目关联的自荐信。
他盯着那个空白文档,光标在闪动,像一种无声的催促。
他还有什么理念可言?
他的“界”在哪里?又该如何去“破”?
那些被他强行压抑的、关于过去的碎片,开始不受控制地翻涌。威尼斯的雨,画廊库房的寒冷,雪山木屋的绝望,还有……那个人沉默而沉重的爱,和决绝离开的背影。
他的“界”,不就是他自己筑起的那道,用悔恨、自卑和恐惧垒成的高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