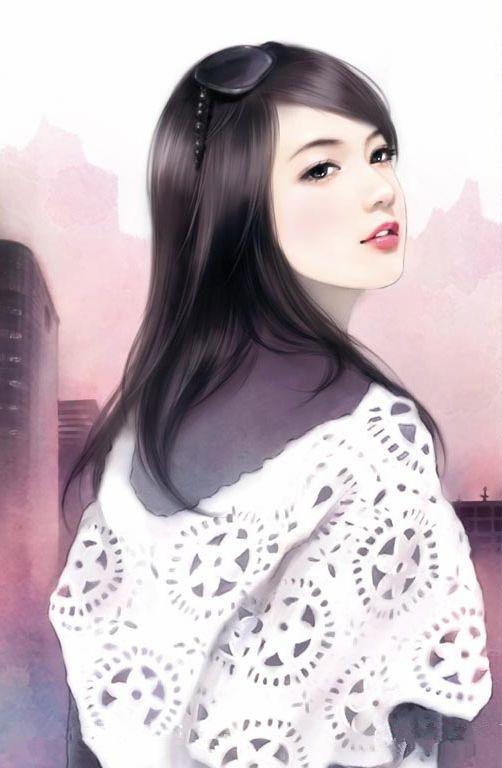紫夜小说>重生后前夫全家也重生了by跃青 > 第41章 第 41 章 勿向外求(第3页)
第41章 第 41 章 勿向外求(第3页)
“大娘言重了。”她声音依旧平和,不紧不慢,“我知大娘本心并非险恶。只是那巴豆粉,性极峻猛,若摄入过量,轻则伤及脏腑,元气大损,重则耗竭真元,危及性命。若非有人从中蛊惑挑唆,大娘又岂会甘冒此等大险,以自身性命为注,来构陷于我?”
孙桂芳端着药碗的手猛地一抖,褐色的药汁泼洒了些许在衣襟上,她骇然失色:“竟丶竟如此凶险?那……那我现下可有大碍?
“那杀千刀的!他拍着胸脯跟我保证这东西顶多让人拉两趟肚子,屁事没有!还说……还说等你们这医馆关门了,他就在对面开间大客栈,所有饭食都包给我做!我……我是猪油蒙了心才信了他啊!”
“‘他’……是谁?”孟玉桐试探问道。
“就是八珍坊那个挨千刀的掌柜,郑辉!”
孙桂芳咬牙切齿,“他说他背後有通天的靠山,我要是不照做,他就让我这饭馆立刻关门滚蛋!我也是走投无路了,妹子!好妹子,你快救救我!
那药是刚煎好的,正烫着,她顾不上吹,她一边说,一边生怕晚了似的,捧着药碗“咕咚咕咚”几口灌了下去,烫得她龇牙咧嘴。
一口气将药喝了,她放下药碗,一把抓住孟玉桐的手腕,如同抓住救命稻草般苦苦哀求:“除了这碗药,还要吃别的什麽灵丹妙药不?”
孟玉桐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安抚道:“莫慌。眼下虽无性命之忧,但为防落下病根,伤了根本,最好往後一个月,每日来服一碗调理脏腑丶固本培元的汤药。”
“好好好!我一定来!日日都来!多谢妹子!多谢妹子救命!”孙桂芳忙不叠地应承,感激涕零。
她如释重负,擦了擦嘴准备离开。
孟玉桐却出声唤住她:“孙大娘留步。今日诊金加上这碗药钱,共计一百文。後续一月汤药,每日三十文,总计九百文。劳烦大娘回头将这一贯钱提前结给白芷,我们也好预备药材。”
孙桂芳脚步一滞,被这数目惊得倒抽一口凉气。
竟要这麽贵?
节省抠搜惯了的她下意识便想开口说不治了。
可一回头瞧见孟玉桐气定神闲的表情,想到她方才描述的巴豆药效之恐怖,再想想自己这条老命,终究是惜命的念头占了上风。
她咬咬牙,挤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成……成!我这就回去凑钱,凑齐了立马送来!”
孟玉桐颔首应允。就在孙大娘转身欲走之际,她清泠的声音再次响起:“孙大娘,‘桂芳’二字,起得极好。桂花性耐苦寒,偏于深秋霜重之时凌寒而放,幽香自远。
“可见境遇再艰,只要自身根骨硬朗,自有芬芳动人处。人活一世,与其眼巴巴指望他人施舍活路,不如反躬自省,精进己身,勿向外求。
“庆来饭馆若想重拾昔日食客盈门的光景,归根结底,还在您二位掌勺人的手上。将那竈台上的功夫拾掇好了,味道才是留住客人的根本。”
孙桂芳身形一震,猛地停下脚步。
这番话,字字句句如同重锤,落在她耳边,打在她心头!
她家饭馆……十年前也曾宾客满座,热闹非凡。
是从什麽时候开始,他们夫妻俩变得懈怠了呢?
再也听不进食客的抱怨,只顾着埋怨时运不济丶人心不古。
竈台上的心思也懒了,火候也糙了,那饭菜的味道,一日不如一日。
丈夫吴庆来总嘟囔是如今人口味刁钻了,可仔细想想,客人变了,他们难道就没变吗?
分明是他们自己没有当初的那颗心了。
十馀年掌勺磨出的厚茧摩挲着粗布衣角,一股混杂着羞愧丶懊悔与茫然的情绪汹涌而来……
她缓缓转过身,对着孟玉桐,极其郑重地丶深深福了一礼,声音带着哽咽:“……多谢妹子金玉良言!”
说罢,她低着头,脚步虚浮地往外走,心神恍惚间,竟差点撞上门外静立的纪昀,慌忙低声道歉後,便失魂落魄地奔回对面饭馆。
孟玉桐这才瞧见不知在门口伫立了多久的纪昀。
她起身,款步走到门边,杏黄的衫子在夕照下泛着柔和的光晕,唇角噙着一丝若有似无的笑意:“纪医官怎麽来了?”
纪昀眉峰微蹙,眸色沉沉,周身却似散发着一股清冷肃然之气。
他薄唇轻啓,带着几分劝诫:“孟姑娘方才对那妇人所言巴豆之害,未免危言耸听。此物虽峻猛,然其效过则自止,何至于脏腑受损丶需月馀汤药固本培元?
“医者仁术,贵在诚笃。虚言恫吓,以牟财利,此乃违背‘医者仁心,贵乎诚笃’之训,失却‘大医精诚’之本分。”
孟玉桐闻言,非但不恼,反而低低笑出声来。
她顺势倚靠在门框上,姿态是难得一见的慵懒随意,那道笑容明媚张扬,如同一朵带刺的花在暮色中灼灼绽放。
“哦?”她尾音微扬,带着一丝戏谑,“纪医官是以什麽身份,在此训诫于我?”
这般情状与传闻中那位规矩内敛的闺秀判若两人。
纪昀脑中蓦然闪过青书的话:孟氏女幼失慈母,父不理事,随孟家老太太长大,素以端方娴静闻名……
如今看来,这般贤名倒像是副极好的面具。
他压下心头那丝异样,“孟小姐误会了,纪某断无训诫之意。只是身为同行,见姑娘行止有违医德,不免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