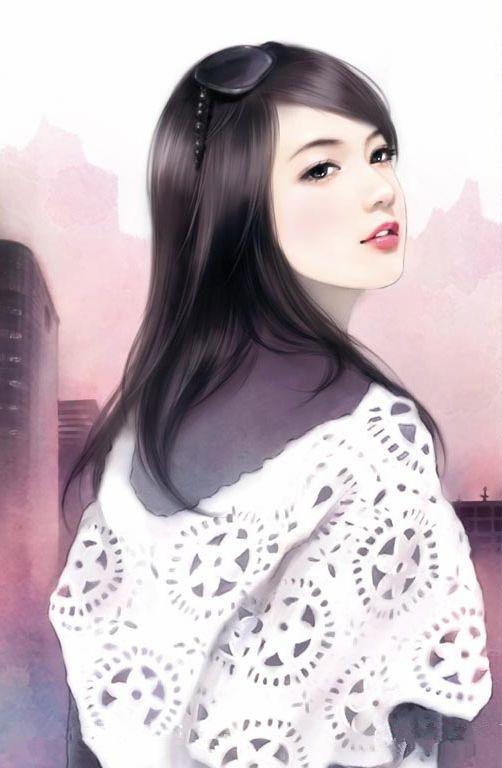紫夜小说>重生后前夫全家也重生了by跃青 > 第41章 第 41 章 勿向外求(第4页)
第41章 第 41 章 勿向外求(第4页)
孟玉桐心下了然。纪昀此人,心中自有一套对“医者”近乎苛刻的圭臬:悬壶济世,一视同仁;言必有据,不欺不瞒;不可见利忘义,不可草菅人命……条条框框,比她前世读过的《女诫》还要严苛几分。
她唇角忽然弯起一道淡然的弧度,语声飘渺:“纪公子觉得,我方才点醒孙大娘的那番话,值不值那一千文?那可是……”
金色的馀晖温柔地镀在她如玉的脸庞上,勾勒出优美的轮廓。她擡起头,望向天边燃烧的流霞,霞光落入她眼中,折射出绮丽的光。
“那可是我用命才换来的道理。如今这般轻飘飘地告知于人,我还觉得亏了呢。”
她的目光从远处收回,站在台阶上,静静看着他。
那双清澈的眸子里,竟似有经年风霜呼啸而过,沉淀着令人心口微滞的冷沉。
用命换来的道理……
勿向外求……
“孟姑娘此言何意?”他下意识追问,声音里带了一丝自己都未察觉的紧绷。
孟玉桐却已收了方才神色,看向他眼下的淡淡青影,语气似乎变得轻快起来,甚至带上点促狭:“纪公子上回不是说用了我的香方麽?怎麽瞧着这几日反倒像是未曾安枕的模样,莫不是那方子对公子不起作用?”
她擡指遥遥点了点柜台上的香囊塔,“喏,如今我们卖的是改良新方,效用更胜从前。纪公子要不要买一个试试?”
那“买”字,咬得格外清晰。
“买一个?”纪昀眉头几不可察地一蹙,似有几分难以置信。
她性子大方周全,对四周街坊丶前日来送副本的陈玢丶云舟丶还有母亲都慷慨赠囊,为何到他这里,便是让他‘买’一个。
她对自己为何如此……如此厚此薄彼。
“是啊,”孟玉桐笑意盈盈,接得飞快,“买一个。”
“不必了。”纪昀断然拒绝,声音恢复了惯常的清冷。
他心头涌上几分烦躁,不欲在此继续待下去,他侧身朝医馆内唤道:“云舟。”
云舟不知正与白芷说什麽,说得眉飞色舞。
一听见纪昀喊他,他忽然一个激灵,同白芷道了声别,连忙应声跑出,出门时还不忘朝孟玉桐咧嘴笑了笑:“孟姑娘,昨日多谢你的伞,我们先告辞了!”
纪昀已转身离开,云舟飞快跟上,两人向清风茶肆走去。
“公子,”云舟憋不住话,“您方才瞧见庆来饭馆那孙氏没?小的方才在里头,可听白芷说了件大事!今日照隅堂开馆,那妇人竟跑来闹场,一口咬定孟姑娘送的香囊有毒,险些闹出大乱子呢!”
云舟见他在听,便竹筒倒豆子似的,将白芷绘声绘色描述的场面,比如孙大娘如何哭嚎指控丶孟玉桐如何破局当衆揭穿的细节仔仔细细复述了一遍。
末了,他还忍不住摇头晃脑地评价:“公子您说,那李世子也忒没气度了!堂堂世子爷,跟孟姑娘一个小娘子计较这些,还使出这等下作手段,真是……啧啧。”
纪昀方才在门外虽听了个大概,此刻方知今日竟发生了这样的事。
他脚步未停,声音淡淡:“孙氏所为,是李璟手下郑辉指使?”
“正是!”云舟用力点头,语气愤然,“依小的看,孟姑娘就是太心善了,那等黑心肝的妇人,害她不成反害己,就该让她自生自灭去。何苦费心给她诊治?治好了也是个祸害,下回被人一撺掇,指不定又出什麽幺蛾子。”
勿向外求……
这四个字再次无声地滑过纪昀心间,此刻却仿佛带着沉甸甸的分量。
躯壳之疾,针石可解;然心魔之困,贪嗔痴妄交织,如附骨之疽,驱使凡夫背离良知,行差踏错,才是真正的顽疾。
他下意识地顿住脚步,回眸望去。
照隅堂门前,已不见孟玉桐的身影。
唯有那方簇新的“照隅”牌匾,在淡金色的夕照馀晖中,仿佛被熔铸了一层流动的金边,光芒流转,竟令人一时难以直视。
或许……她方才点醒孙桂芳的那番话,其价值,确实远超千文。
是他狭隘了。
恰在此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自新开门方向传来。
只见一男子骑快马飞驰而至,在照隅堂门前勒缰停住。
马上男子动作利落地翻身而下,风尘仆仆,却精神奕奕,冲着馆内高声喊道:“崔大!梅三!还不快滚出来迎你们少当家!”
云舟好奇望过去,一回头,正瞧见崔大成和梅三如同离弦之箭般从馆内冲出,激动地围着那男子又捶又抱,口中高喊着:“少当家的!您可算回来了!”
“原来这位就是刘思钧,那些游商的领头人。果然意气风发,威武不凡!”云舟恍然,对纪昀道,“瞧着他们跟孟姑娘这边,亲热得跟一家人似的。”
纪昀只淡淡看了一眼,便转过头去,仿佛未曾听见,径自往前走了。
云舟回过神,赶紧小跑着追上去:“公子!等等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