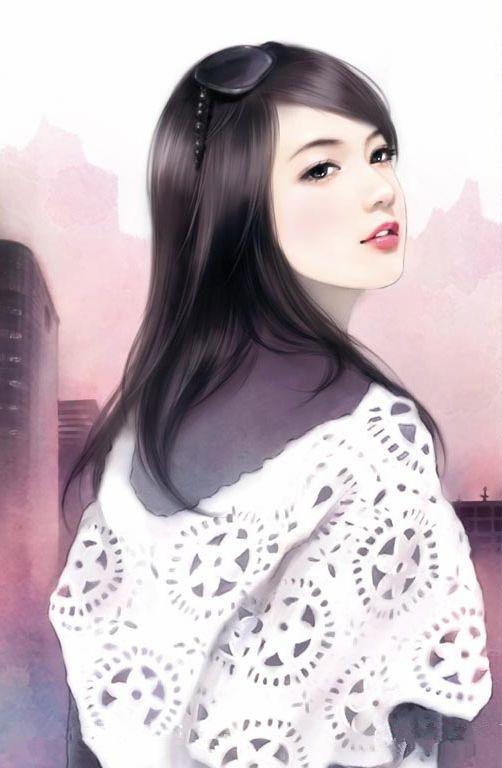紫夜小说>丙丁柴窑 > 第39章 恰空 他又何尝不是一只容器(第3页)
第39章 恰空 他又何尝不是一只容器(第3页)
恰空在最开始时,只是一首节奏为三拍子的舞曲。随着17世纪传入意大利,它开始作为一种成熟又极富表现力的音乐结构而广为流传。
有无数乐曲家曾以此为定调,创造了许多作品。他们把自己的灵魂,装进了“恰空”的骨架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乐曲。
中间接连的变奏时强时弱,像呜咽又像抽泣,一点一点将音乐推向高潮。
琴弓和琴弦的每一次拉扯都像是理智与情感的互搏,激情地上扬又飞速地落下。
矛盾与纠结在翻飞的琴弓□□现得淋漓尽致。
暗室里留了一盏昏黄的落地灯。
顾寅言给自己倒了杯红酒,在落地窗前的沙发里坐下。
他仰头抿了口,红酒的涩味很苦,回甘却绵长。
梁亦芝的那张拍立得,被他攥在掌心,卡纸的四角微微蜷起。
顾寅言看着它,大拇指在卷翘的边角处来回地摩挲,想把它抚平。
他极轻地从鼻腔里叹了一声。
差点就要被她拿回去了。
顾寅言听了会儿,心头被乐曲炽烈的情绪充盈得满涨。他又走到唱片机前,换掉了音乐。
下一首曲子,他也已经听过了不下百遍。
这首音乐没有旋律,仅是简简单单的念白和叙述。
他在国外那几年时,都是伴着这首独一无二的曲子,消磨时间丶锻炼心志。
顾寅言边听,边轻轻晃了晃手里的酒杯。
他端着杯子,垂眸打量。里面的液体晃荡来去,水平面始终保持着与地面平行。
他忽然生出一种错觉,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一只容器,想把他渴望的丶期盼已久的,全都装进去。
只是他拥有的实在很少,所以哪怕是一点点,他都想竭力保存好。
-
次日。
顾寅言今天起得很早,开车去机场接一个人。
他到得早,但没提前下车,在车里坐着,等待时间差不多了,才出发去航站楼。
他双手插在大衣的口袋里,站在出口处。
不多时,里面出来一个女人。长发全部束起盘在脑後,发际线和额前都用发胶打理地干净,没有一丝碎发,利落整齐。
驼色风衣的扣子扣在最上端,腰间系着系带轻轻舞动。
那女人的五官虽然和他没那麽像,可细看就能发现,两人的脸型丶鼻梁高度甚至唇形都如出一辙。
见到顾寅言,她步伐果断地迈向这里。
于榕眉梢微挑:“让你来接我,没想到你还真来了。”
顾寅言回:“看来是我会错意了。”
于榕握着行李箱的扶杆,推给他,
顾寅言顺势接过。
他又问:“呆多久?”
“一周吧。”
“有点久。”
于榕侧过头,睨了顾寅言一眼:“怎麽?你有事瞒着我?”
顾寅言没回答她的疑问,他带她来到停车场,问:“准备住哪?”
于榕上了车,应道:“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