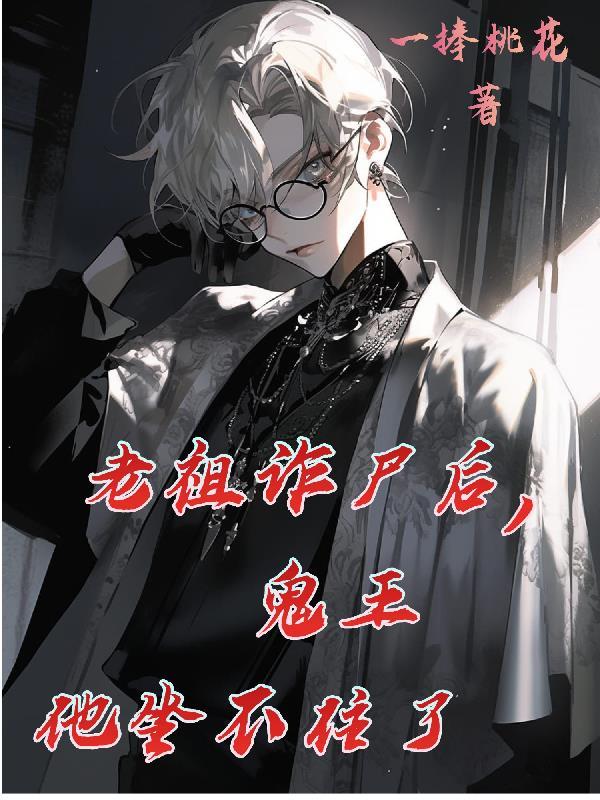紫夜小说>恋与深空官服在哪下 > 第40章 你护着她我放心(第1页)
第40章 你护着她我放心(第1页)
翌日。
摘星楼顶层风穿檐角,风铃轻响。
夏以昼踏着紫檀木阶上来时,皂靴碾过残落的桂花瓣。
声响轻得未扰到窗边对弈的人。
黎深正执白棋落子,素白指尖捏着棋子悬在棋盘上方。
侧脸线条冷硬如精心雕琢的玉,墨松松用玉簪束在脑后。
几缕垂在颈侧,随着呼吸微晃。
听见动静,他眼尾都未抬,只淡淡道:
“二皇子倒是稀客,竟寻到这地方来。”
夏以昼站在三步外,珊瑚赫色的常服衬得他肩宽腰窄。
唇边噙着稳沉的笑,指节叩了叩腰间挂着的青瓷酒壶:
“再稀,也得来找你这躲懒的。”
话音落,他手腕轻扬,酒壶带着破风的轻响朝黎深飞去。
黎深终于抬眼,眸色如深潭,左手微抬。
精准扣住壶颈,动作利落得没让壶中酒液晃出半分。
指尖触到壶身温热,他才瞥了眼壶底刻的“千金焕”三字,眉梢微挑:
“舍得把这酒拿来,怕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不愧是国师的关门弟子,在你面前可没有秘密可言。”
夏以昼走到对面落座,随手拿起颗黑棋把玩,指腹摩挲着棋子冰凉的触感。
“当年你走时说三年归,结果一去快五年。
回来就躲在摘星楼里下棋,我若不来。
你是不是要等到明年开春才肯见人?”
黎深将酒壶放在桌角,落子定了棋盘一角:
“京中喧闹,不如这里清净。”
他抬眼时,目光扫过夏以昼。
对方坐姿端正,下颌线清晰。
哪怕只是随意坐着,也透着皇子的沉稳贵气。
倒与自己这清冷性子相得益彰。
也不怪两人那么多年的友情,见的面寥寥无几,却依旧如故。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叙旧。
从当年在玄都观论道,到黎深在山中修行的趣事。
夏以昼话多些,黎深偶尔应一句,却也没冷了气氛。
风卷着桂香进来时,夏以昼忽然倾身,手肘撑在桌上,眼底带着几分促狭:
“黎深,这壶千金焕可不是白送你的。”
黎深执棋的手一顿,抬眸看他,眸光清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