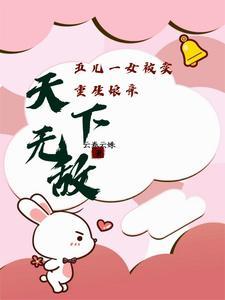紫夜小说>今天小狐狸吃鱼了吗? > 秋雨连绵检验渠身(第1页)
秋雨连绵检验渠身(第1页)
秋雨连绵,检验渠身
夜雨缠缠绵绵下了三日,河谷里的水汽漫上来,连帐帘都润得发潮。
凌延天不亮就披了蓑衣,踩着泥泞往渠沟走。刚转过山坳,就见老河工正蹲在渠边叹气,手里的木尺插在泥里,尺身没入半截。
“怎麽了?”凌延走过去,靴底碾过湿滑的卵石,发出细碎的咯吱声。
老河工指着渠底,声音里带着焦愁:“大人您看,这雨下得邪乎,渠沟里积了半尺深的水,有些地段的红泥层泡得发涨,都能攥出浆来了。”
他用木尺拨开表层的积水,底下的红泥果然软塌塌的,指尖按下去就是一个深坑。
“再这麽泡着,之前夯的地基怕是要松了。”
凌延蹲下身,掬起一捧渠水,水色浑浊,带着细碎的泥渣。
他把手放在鼻尖闻了闻,没有异味,倒是混着些草木的清气,这说明渗水还不算严重,主要是雨水淤积。可他指尖触到渠壁,土块竟簌簌往下掉,指甲缝里立刻塞满了湿泥。
“东边那段高坡呢?”凌延忽然想起渠沟最东段的斜坡,那里是黏土混砾石的结构,本就怕水泡。
老河工脸更沉了:“刚让人去看过,坡底塌了一小片,有辆运石料的板车陷在泥里,拉都拉不出来。”
凌延站起身,蓑衣上的雨水顺着下摆往下淌,在脚边积成小小的水洼。
他望着连绵的雨幕,远山隐在白雾里,连雪山的轮廓都模糊了。这雨来得不是时候,渠沟刚挖成雏形,最怕的就是长时间浸泡。
他声音透过雨帘传出去,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让民夫们分两队,一队拿铁锹挖排水沟,沿着渠沟两侧挖一尺深的明沟,把积水引到下游的河道里;另一队取干草和碎石,先把塌坡的地方垫起来,再用木夯把软泥重新夯实。”
“可这雨没停的意思,干草怕是不够用啊。”老河工皱着眉,营地里的干草本是用来铺棚子的,这几日烧火取暖用了不少。
凌延望向河岸的柳树林,雨里的柳枝绿得发暗,枝条垂到水面上,荡起一圈圈涟漪。
“让石匠们暂停凿石,先去砍柳条。”
他指了指那些柳树,“把柳条编成筐,装满碎石,沿着渠壁码两排,既能挡水,又能护着红泥层。”
老河工眼睛一亮:“这法子妙!柳条遇水会发涨,反而能贴得更严实。”
他刚要转身,又被凌延叫住。
“告诉大夥,雨里干活加两合米,每人发块姜,煮姜汤驱寒。”
凌延解下腰间的水囊,塞到老河工手里:“你年纪大了,别淋太久,让年轻力壮的多搭把手。”
老河工捏着温热的水囊,喉咙有些发紧,只重重应了声“哎”,便踩着泥水往营地跑。
凌延沿着渠沟往东走,雨丝打在脸上,带着凉意。渠底的积水没过脚踝,每走一步都要陷进泥里,拔出来时靴底沾满了红泥,沉甸甸的。
快到东段高坡时,果然听见一阵吆喝声,几个民夫正拽着板车的绳子往坡上拉,绳子绷得像弓弦,车辙在泥里碾出两道深沟,车轮却纹丝不动。
“别硬拽!”凌延喊了一声,大步走过去。
板车的轮子陷在塌坡的泥坑里,辐条上缠着湿漉漉的草根,车斗里的石料滚了大半,青灰色的石头上蒙着层泥浆。
“大人,这泥太滑了。”滁州的里正抹了把脸上的雨水,满脸急汗,“石料运不到滚水坝,那边就没法砌坝基了。”
凌延围着板车转了一圈,指着坡侧的空地:“去砍些粗树干来,垫在车轮前,再把碎石铺在树干上,做成简易的滑道。”
他蹲下身,捡起块碎石塞进车轮下的泥坑,“先把车斗里的石料卸一半,轻些好拉。”
民夫们七手八脚地卸石料,又扛来树干铺在泥里。凌延也挽起袖子,和他们一起拽绳子。粗麻的绳子勒得手心发疼,雨水顺着胳膊流进袖管,凉得刺骨,可他心里却烧着一团火。
号子声在雨里荡开,混着车轮碾过树干的咯吱声,板车终于一点点往上挪,最後“哐当”一声滑上了坡顶。
“成了!”民夫们欢呼着,脸上的泥水混着笑容,竟比晴天时更有精神。
凌延甩了甩手上的泥,刚要说话,忽然听见身後传来“哗啦”一声响。转头一看,竟是渠壁又塌了一块,湿泥裹着碎石滚进渠沟,溅起半人高的水花。更糟的是,塌落的地方露出了之前用麻丝和油灰堵的缝隙,此刻正有浑浊的水往外冒,像一道细细的小泉。
“坏了!”老河工也赶了过来,脸都白了,“这缝怕是被雨水泡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