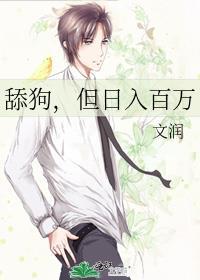紫夜小说>今天小狐狸吃鱼了吗? > 汛退渠成静待归期(第2页)
汛退渠成静待归期(第2页)
这句话像粒暖珠,滚落在凌延心里,熨帖得他四肢百骸都透着暖意。
他收紧手臂,把人抱得更紧些,远处民夫们的谈笑声丶渠水流动的哗哗声丶风吹柳苗的沙沙声,都成了这片刻温情的背景音,温柔得让人心头发软。
收拾行装的那日,河谷里飘着淡淡的桐油香。
民夫们三三两两地聚在库房外,把剩下的石灰丶碎石清点入库,石匠们坐在空场上,打磨着最後几块边角料,凿子敲击石头的叮当声清脆悦耳,连库房里的空桐油桶都被码得整整齐齐,桶身上的木纹在阳光下清晰可见,像记录着这段日子的点滴。
何知洲坐在工棚的木板床上,正把那几本治水旧案和《河防考》仔细包进蓝布包袱里。
他的动作很慢,指尖划过书页边缘时,会下意识地停顿片刻,那本《河防考》的封皮已经磨得有些发白,书脊处用线重新缝过,是他前些日子见书页松动,特意找夥房的大婶要了针线缝的。
翻到其中一页时,他忽然停住了,那是凌延帮他改批注的地方,凌延的字笔锋凌厉,与他自己清秀的字迹落在一处,倒像是两种不同的风骨在纸上交相辉映。
他指尖在那些字上轻轻摩挲,忽然擡头,见凌延正走进来,手里拿着两件新做的棉袍,便笑着扬了扬下巴:“你这字,在泥地里练得更有力了。回去之後,该给我写幅楹联。”
“想要什麽内容?”凌延走过去,顺手把其中一件棉袍往他身上披了披,棉袍是用厚实的棉布做的,里子还加了层薄棉,带着阳光晒过的温度,他小心翼翼的叮嘱:“河谷风凉,仔细又着凉。
何知洲拢了拢衣襟,鼻尖萦绕着棉布与阳光的气息,心里暖融融的。他想了想,眼底闪过一丝笑意:“就写‘XXXXXXX,XXXXXXX’。把咱们在这儿做的事,都写进去。”
“好。”凌延应着,帮他把包袱放进随身的木箱里,扣箱锁时,忽然像是想起了什麽,从怀里摸出个小布包,递到他面前说:“路过州府时买的,给你。”
布包是用素色的棉布缝的,系着个小巧的结。何知洲解开时,心跳莫名快了几拍,里面是枚玉坠,玉色温润,雕着两支纠缠的柳条,柳丝蜿蜒交错,像极了他们此刻的牵绊。
“配你。”凌延的声音有些低,耳尖微微泛红。
何知洲接过来,指尖触到玉坠的冰凉,心里却烫得厉害。
他低头,借着窗缝漏进的阳光仔细看着,忽然从自己的行囊里翻出个同样的小布包,打开,里面是枚一模一样的玉坠,只是雕的柳条方向相反,恰好能与凌延给的那枚合在一起。
“那你也得戴个配对的。”他说着,踮起脚,把玉坠往凌延颈间一挂,冰凉的玉贴着凌延的皮肤,两人的指尖不经意间碰到一起,像有电流窜过,烫得人心头发颤。
凌延低头看着颈间的玉坠,又看了看何知洲腰间那枚,忽然伸手,把他揽进怀里。
工棚外的风顺着门缝吹进来,带着桐油的香气,两人相拥着站在光影里,听着外面民夫们的说笑声,忽然觉得,这简陋的工棚,竟比京城的高堂华屋更让人安心。
啓程那日,天刚蒙蒙亮,河谷里的炊烟就比往常稠了些。
夥房的烟囱里冒出的烟柱在晨光里散开,混着早饭的香气,飘得很远。
老河工带着民夫们早早地站在渠边,手里捧着新晒的柿饼和核桃,见凌延和何知洲走来,便纷纷上前,把手里的东西往他们行囊里塞。
“大人,这柿饼是俺家婆娘晒的,甜得很,路上饿了能垫垫肚子!”一个年轻的民夫把布袋往凌延手里塞,脸上带着憨厚的笑。
“先生,这核桃是山里摘的,补脑!回去路上看书累了,就砸两个吃!”另一个民夫往何知洲怀里塞了个布包,布包上还绣着朵歪歪扭扭的花。
老河工站在人群最前面,手里捧着个陶罐,罐口用红布盖着,见两人过来,便把陶罐递过去,眼眶红红的:“大人,先生,这是河谷里的新米,俺熬了些米糕,路上能吃。你们……明年开春可一定来啊!我给你们留着最甜的柿饼,等着看柳苗抽条!”
“一定来。”凌延接过陶罐,指尖触到罐身的温热,点了点头。
何知洲站在他身边,正悄悄往他手心塞了颗核桃,核桃的纹路硌着手心,却带着让人安心的触感。两人相视而笑,目光里的暖意像晨光里的渠水,温柔得快要溢出来。
马车啓动时,何知洲掀开窗帘回头望了一眼,滚水坝的石基在晨光里闪着光,渠水静静流淌,两岸的柳苗在风里轻轻摇曳,像在挥手说再见,又像在盼着春暖花开时的重逢。
民夫们还站在渠边,身影在晨光里拉得很长,老河工的声音顺着风飘过来:“大人!先生!一路顺风啊!”
马车驶出河谷时,地势渐渐平缓,远处的雪山在晨雾里显出朦胧的轮廓,像幅淡墨画。
何知洲忽然掀开窗帘,望着那雪山渐渐缩小,直到变成个模糊的白点。
凌延从身後轻轻环住他的腰,下巴抵在他发顶,发间的清香萦绕在鼻尖,让人心里踏实。“在想什麽?”他低声问,声音裹在马车行驶的轱辘声里,格外温柔。
”“在想,等回了京城,就把咱们在这儿的事画成画。”何知洲转头蹭了蹭他的脸颊,鼻尖碰到他的下颌,带着微凉的触感。
“画里要有夯土的号子,有你帮我调灰浆的样子,有工棚里的油灯,还有这两岸的柳苗。”
凌延收紧手臂,把人往怀里带得更紧些,指尖触到他腰间的玉坠,又碰到自己颈间的那枚,两枚玉坠轻轻相撞,发出叮当一声轻响,像两颗心在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