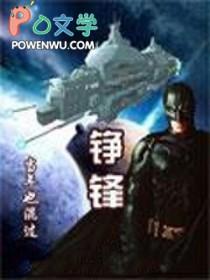紫夜小说>四方来食夕禾完结了吗 > 9 偷梁换柱(第1页)
9 偷梁换柱(第1页)
9。偷梁换柱
「月亮粑粑,乧里坐个嗲嗲;
嗲嗲去克买菜,乧里坐个奶奶。
奶奶出来绣花,绣个糍粑;
糍粑跌到井里,变成月亮」
尽管许多外地人未曾踏足湘省,但他们大多听过这首源自当地的民间童谣。
小时候,何应悟的娱乐方式寥寥无几,一台二手的背投彩电几乎承包了他所有的闲暇时光。
在网络平台尚未兴起的年代,湘省的芒果台凭借几档自制节目迅速崭露头角,成为卫视领域的佼佼者。当时,娱乐节目选择有限,每逢周五丶周六的晚上,何应悟便和弟弟妹妹们互相督促早早写完作业,定点守在电视机前,收看诸如《快乐大本营》《越策越开心》这类潭州本土的节目。
读书那会儿,有几个同专业的学长学姐进了潭州本地的电视台实习,可给何应悟羡慕坏了。
为此,哪怕因为连夜赶车困得上下眼皮打架,何应悟还是坚持拉着不情不愿的谈嘉山,跑到湘省卫视这座新传学子耶路撒冷打卡点拍了一大堆游客照。
这些照片,也顺利成章地成了次日何应悟赖床的理由。
一大早,刚从河边晨跑回来的谈嘉山拎着两碗加量炒码的麻辣牛肉扎粉,怒气冲冲地用肩膀撞开门:“这里是刘阳,又不是潭州市区,我去哪儿给你买臭豆腐和糖油粑粑?”
何应悟人虽醒了,但魂还在睡。他明白谈嘉山是在拐着弯邀功丶并非真生气,不仅不带怕,还心安理得地打了个大大大哈欠。
他拖着椅子挨到谈嘉山身边,接过对方拆好的筷子,擡起脸眯着眼睛问:“你吃过了吗?没吃的话,我们合吃一碗。”
“吃过了。”
被这麽一打岔,好糊弄的谈嘉山的怨气去得也快。他顺手揉了揉何应悟还没来得及打理的乱糟糟卷发,催促道:“快吃,吃完了好出门干活。”
何应悟昏昏沉沉地应了一声,低着头吃粉。
他的头一低,那一丛卷发看起来手感更棒了。何应悟的发质本来就好,发量又多,手指一伸进去,还带着体温的头发便会打着旋儿地乖顺绕上来。
谈嘉山明明才号过一回,却还是忍不住盯着对方头顶发呆,手指也不自觉屈了一下。
收到消息,赶过来吃早餐的杨钰嫌这口父子情深的画面不下饭,嘀嘀咕咕地端着粉走远了。
。
常言道,湘省方言“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语”;而湘菜的味型,似乎也延续了这一传统。
在泰斗王墨泉的研究下,味型繁多湘菜被大致归纳为腊香丶豉香丶瓿坛香丶臭香丶霉香等33种基本类型。
相比滇菜的酸辣丶蜀菜的麻辣,湘菜在辣度方面的战斗力并不突出,更多的是强调菜品的香气与适口性。
发源于大围山的刘阳菜,便是这一风味的典型代表。
此次行程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一家连续五年蝉联金筷子评级的刘阳菜馆进行降级评审。
“他们家今年的评分下滑得很快,已有两组评审员给出了铜筷子的评价。”杨钰将笔记和前期调研报告递给後座的两人,补充道,“我们是最後一组,而且谈嘉山和我的评审权重较大,试菜时得格外谨慎。”
何应悟点点头,翻开文件开始细读。
餐厅地处偏僻,出租车司机在城中村绕了快半小时,才把三人送到终点。
这家店开在老城区尽头的筒子楼底商之间,与周边那些仿佛从千禧年停滞至今的陈旧建筑相比,它的装修的痕迹格外明显,崭新得甚至有些格格不入。
推开那扇做旧样式的木门,迎面扑来一阵混合了腊香丶油香丶菜香味道的热烫蒸汽。
“欢迎光临姐弟蒸菜馆!”
人未至声先到,几人找到空位坐下,穿着仿苗族服装的服务员这才懒散地迎了上来。
“扫码点单哈。”不知道是不是人太多了,服务员的态度不算太好,几人催了几回,她才把水盅端上来。
见何应悟背着个大书包,服务员眼睛一转,话里话外带着点炫耀的意思:“你们都是来旅游的吧,我们家也算是刘阳最出名的馆子了,挺有眼光的。吃不了辣的话,选微辣吧!”
“不用,做正常辣就好。”何应悟边给另外两人烫碗,边说。
“乖。”谈嘉山接过还有些烫手的碗筷,把手机递过去,“你们再挑几个,小鸟选点清淡的。”
“好哦。”
何应悟同杨钰凑到一块,研究了好一会儿才点好单。
“这家蒸菜馆里的顾客,好像大部分都不是本地人。”等菜的空隙,杨钰百无聊赖地环顾四周,观察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应该都是来旅游的——说什麽方言的都有,偏偏没听见有人讲刘阳话。”
谈嘉山点点头,说:“但在之前的笔记里有提到,这家店最初是作为大围山蒸菜的金字招牌店提报上来的,本地认同度应该很高才对。”
“上菜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