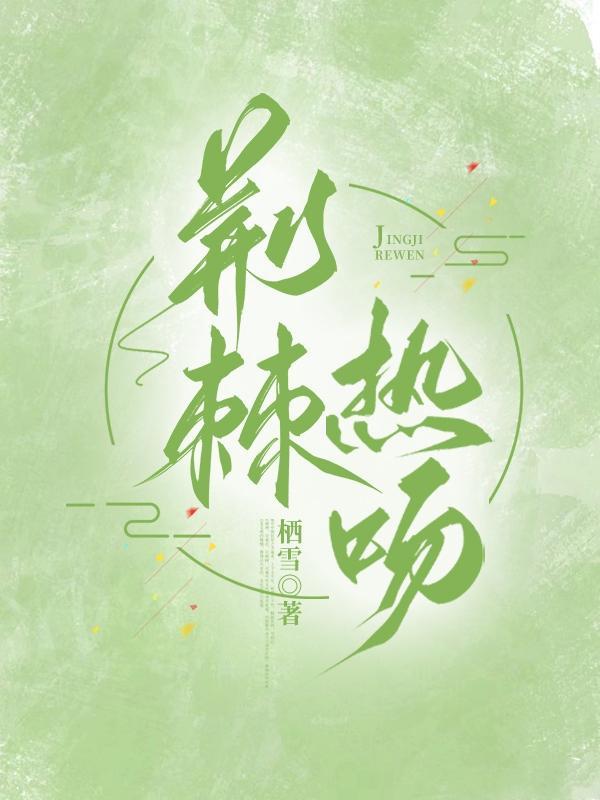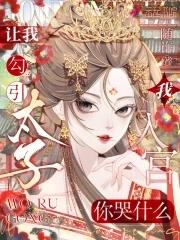紫夜小说>春季到来绿满窗图片 > 止水将(第4页)
止水将(第4页)
经过这最後一道程序,一棵棵山芋秧子在阳光下站立了起来。虽然那秧苗枝叶有些打焉儿,但是毕竟是迎着微风站立了起来。一棵棵,翠绿的,为这春日的西岭增添了生气。黄土垄上,是一棵棵幼小的秧苗,黄土陇下,是山里人憋着的期望。
山芋秧子很争气,很快地生长,亭亭净植的秧苗越长越长,直至匍匐丶蜿蜒在山芋沟里,生出苍劲的根须,紧紧抓住西岭那贫瘠的土地,精壮的身躯顶着双排的叶子,整个山芋地里是一片的翠绿。
山芋沟里会有瞎杧茧,说不定还会有蛇。有人看见山芋沟里的“白了线”,也就是白蛇,追着人跑,比人窜地还快。人在山芋沟里跨出一大步,它早已“飞”到人的前头了,像是有了道业。听了这些,我很是害怕,觉得那是电视剧里的白娘子来到了山芋地里。每次跨过山芋沟,我都是飞快地跳走。山芋秧子长得壮,说明山芋沟里的山芋长得好。
十月里,刨山芋了。家家户户,老头子老嫲嫲,壮劳力小夥子,小媳妇大闺女,推着胶车子,扛着头丶挠鈎,全到地里去。拉起头丶挠鈎刨起来吧。“砰”一下下去,粉皮丶白肉的山芋就露出了头儿。再下去一头,连土带山芋就一起带了出来。刨山芋的弯腰刨,後面的人蹲在地上,拉着筐子拾山芋。满地里都是带着新鲜的泥土的山芋的味道。
有的山芋是多胞胎,一根藤上结地滴啦八挂的,个个都是瘦长身材。有的是双胞胎,拾山芋的人一手拎起两个。这些双胞胎,有的两个都是瘦长型,有的两个都是椭圆的胖子。还有的就是一个独生子,大大的,圆圆的,憨憨的。要是刨的时候没瞄准,“咔嚓”刨在一个胖胖的山芋上,一下劈出来沙白的流着汁水的瓤,那才叫人心疼。
刨出来的山芋都要装车,推回家。推胶车子的人,弯腰,弓背,头埋在盛山芋的筐子底下,咬着牙,在窄窄的几乎无路可走的茅草丛生的山路上,打着滑儿,愣是走出一条路来,低着头推到家。
满西岭的小推车,来来往往,地上是小推车落下的山芋秧子山芋叶子,还有吃地胖胖的瞎杧茧,被车轱辘碾过,发出“砰砰”的声音。瞎杧茧,虫如其名,青绿色的丑陋的大虫子在山芋地里蠕动,吃山芋叶子,女孩子看到它心里总会发毛,要是不小心踩到了更是吓得要命。但是它的蛹像是一颗大花生一样,外头有着棕黄色的油亮亮的壳,壳上还有一圈圈的螺纹。动一动它,它的针尖儿一样的尾巴就会蠕动起来,像是一个裹在包被里头的小娃娃,看起来并不是很可怕。
黄褐色的蛹炒出来香香的。爷爷炒来吃过,我妈妈也炒过。我们把那些黄色的蛹捡来,带回家给我爷爷炒。我爷爷只炒一小盘子,他放的油多,炒好了,一个个油亮亮的,码在盘子里,吃一口儿,香香的。我妈妈炒的多,她一炒一大碗,又舍不得放油,炒好了,一个个干巴巴地堆积在大碗里,吃起来甜甜的,干干的。
秋收了,蚂蚱在地里欢乐地飞,它们鼓起翅膀,像螺旋桨一样飞过去,锯子一样的大腿冷不丁地蹬到人的大腿上,人的大腿上就留下一道红红的印。秋天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因为我们可以逮它们回家。
蚂蚱飞,我们追,扑过去,抓在手里细端详:绿色的蚂蚱绿裙装,那绿裙还有内衬,薄薄银银,闪闪亮亮,是人间天上最漂亮的衣裳。抓住蚂蚱以後,把它两只大翅膀下头的小翅膀各自掐掉一截儿,它就飞不远了。薅一根草棒子,从蚂蚱脖子後头捅过去,把蚂蚱成串儿地插在草棒子上,它就彻底飞不动了。棕褐色的蚂蚱,想必它的肉质也饱满成熟了,回到家下锅里一炒,硬硬黄黄的蚂蚱肉加上大铁锅的油盐味儿丶蚂蚱翅膀的焦糊味儿,真是满嘴喷香呢。
山芋刨回家是要负责的。刨完山芋,家家户户又开始擦山芋干子了。最开始用“擦耪子”擦山芋。“擦耪子”是一个洗衣板那麽大的木板,中间横嵌着一个刀片,那刀片有镰刀刀片那麽大。大人们擦山芋,小孩子跟着把山芋干子装起来,倒到框子里。等把框子装满了,大人再推起胶车子,去地里晾山芋干子。把擦好的成堆的山芋干子均匀撒开,撒到地里,再去把那些重叠的山芋干子挪窝晾开,哪里有缝隙,就再补放几块。
娴熟的大人晾起山芋干子来,蹲在地上,该挪窝的挪窝,该补空儿的补空儿,动作麻利,晾出的山芋干子一片片随机布置,有大有小,浑然一体,灵动飘逸。我可能是因为年纪小的缘故,又或许是天生的死板,就是不习惯这样先挥洒再补充的方式,非要自己提上一篮子山芋干子,从地头开始,一块一块地排,排地笨笨拙拙整整齐齐。
山芋干晾晒在地里。晾完以後就祈祷有几个响晴的好天气,然後再一家子一起,一块地一块地收山芋干子。如果哪天突然来了雨,还要拿起化肥袋子,推起小推车,赶紧去抢收,总不能让这全家的口粮烂在地里吧。有人家夜里还会睡在地里看山芋干子,防止夜里有小贼去偷。收好的山芋如果不看好,放在地里甚至家里,被人家夜里扛走也是有的。所以不得不谨慎。老温的大儿子温如意大爷,他有一次夜里去看山芋干子,自己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听到耳边有动静,等他醒来,发现有人正在偷他家的山芋干子呢。小贼见他醒了,丢下装了半天的山芋干子,出溜跑了,他起来把小贼装好的两袋子山芋干子轻轻松松推回了家。
地里的山芋也是有人偷的。田间地头过往的小孩,看见人家地里露出头的红红的山芋,瞅瞅四下里无人,赶快徒手扒一个出来,拿到空地里,用秫稭棒子盖上,点上洋火烤烤吃。还有一种高手小哥,说是在人家刨完山芋的地里拾人家落下的山芋,但是走到还没有动工刨的山芋地边,看见露出头的胖大山芋,“砰”地一下把头甩上去,收杆起头时,那个胖大山芋就被准确又巧妙地“钓”起来了。
十月里,山芋秧子完成了它的使命,懒散地卧在地里晒太阳,等晒得焦干,晒得发黑,老百姓又该去该拉山芋秧子了。家家户户推着胶车子在西岭上来来回回。也不用筐子,把满地山芋秧垛成一垛,打个捆,系起来,放到小推车上,再用绳子勒紧绑好,小推车一推,不怎麽费劲就推回家了。
黑色的山芋秧子捆成一大捆,绑在胶车子上,一个人推,一个人跟着,走过地头上长满荒草的小路。秋日的阳光照耀在人们的身上,个个都是乐呵呵,微笑着。庄西头的纪臣大爷来推山芋秧子了。纪臣大爷个子高高的,瘦长脸,黄皮肤,他穿着黄绿色的中山装,像个当兵的。纪臣大娘个子矮矮的,留着二道毛子,双眼皮深深的,大眼睛常常笑着。
庄东头,“小猪秧”的妈妈也来了,坐在柿树底下歇歇儿。她穿着粉色的秋衣,笑的最开心,黄黑色的脸上,笑纹挤在一起,像一朵绽开的秋菊。她长得比纪臣大娘年轻,比纪臣大娘懂风情。她在吃糖。纪臣大爷看见她,也要吃糖,她就“咯嘣”一下咬下半颗,递给纪臣大爷。
纪臣大爷对庄亲事邻特别热情,就是对纪臣大娘不好,爱打纪臣大娘。纪臣大娘跟我妈妈是好姊妹。姊妹们经常在一起说说各自的愁肠。
纪臣大爷有一儿一女。大女儿叫燕儿,个子随妈妈,大眼睛,白白的,很秀气,在萝村当小学老师,除了去上班时路过我爷爷家门前,平时不怎麽看得到她。纪臣大爷的儿子长得胖乎乎的,中等个子,很正派的国字脸。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雷锋长得是什麽样子的,但我觉得,雷锋长得应该就是他这个样子的吧。
5。煎饼
山东省,山东省,所多的是大山,是青石板,是窗含西岭千秋石,美则美哉,只是不利于长庄稼。人多,山多,丘陵多,每家的地少,地里的石头多,地土不好,只能种山芋。极少的几块沃土用来种小麦。家家户户吃的是地瓜干碾碎烙的煎饼。
那时候每家锅里煮的最常见的是山芋,手里是白白的甜甜的山芋干子煎饼,里头搭配了小麦丶玉米,透着细小的玫红色地瓜皮,吃起来发甜。
妇女们为了烙煎饼要费好一番功夫。头几天就要淘粮食,把地瓜干儿和要搭配的玉米丶小麦泡泡,淘洗一下,分放在两个铁桶里。条件好的,掺的小麦多一点,条件不好的,掺的山芋多一点。第二天,五更头儿里,天黑沉沉的,我奶奶和几个早就约好的妇女,就呼朋引伴地挑着挑子,去附近的张庄“嗑糊子”去了。张庄到荆堂有五六里路。妇女们走到了张庄,“嗑糊子”那家男的还没起来。妇女们把鈎担和铁桶放在地上,黑夜里排着号等着,等急了就去他家喊人。那男人来了以後,开动机器,妇女们挨个把两个铁桶里淘洗过的粮食,倒进机器的斗子里,机器一声响,白色的糊子就出来了。把糊子刮到桶里,两桶粮食,换来两半桶糊子,挑回家去烙煎饼吧。
到家以後,把桶里的糊子倒进两个瓷盆子里,家里的三脚的鏊子支好了,用自己缝的专门擦鏊子的厚厚方方的大抹布,擦上豆油,把鏊子擦亮了。用干干的麦稭烧热鏊子,左手舀上一勺子糊子,倒在鏊子上,右手拿起烙煎饼的竹撇子,赶着那勺糊子在热鏊子上走一大圈,再朝内循环走几个小圈,直到圈子在鏊子最中间缩成一个小黑点。用竹撇子赶着最後一点糊子,把这最後一片光鏊子顶糊上,顺势把糊子厚的地方刮薄一点,一个圆圆的煎饼就烙成了。鏊子底下填一把麦稭,旺旺地烧起来,鏊子上的煎饼变得黄黄的,香香的。竹撇子打边儿上慢慢撇开一个口子,沿着鏊子慢慢伸进去,将煎饼跟鏊子分开,一整张煎饼就从鏊子上揭了下来。
刚烙好的煎饼香香的丶脆脆的。鏊子顶上烤黄的几片煎饼更香更脆。新煎饼好吃,烙煎饼的妇女可是受了罪。尤其是夏天。可是,全家人不能不吃饭,再热的天气,妇女也要坐在鏊子跟前烙煎饼。身旁堆着麦稭,鏊子底下烧着火,头上顶着太阳,脸上淌着汗。
往前,年头儿不好的时候,有的人家因为穷,就早早地把自家的女孩儿送到了婆家,当人家的“团圆儿媳妇”,因为年纪小,先在婆家养着,等长大了再跟丈夫圆房。也是因为年纪小,所以不会烙煎饼,烙煎饼的时候就是活受罪。“不会烙煎饼啊,摁着鏊子煎,把手煎地血糊酱烂,想想真可怜!”这是“团圆儿媳妇”唱的歌,我妈妈会唱,我奶奶也会唱。
那时候,烙煎饼是每个妇女必备的本领。谁要是不会烙煎饼,就等于吃饭问题没办法解决。人们见了面打招呼,不是说“吃饭了吗”,而是说“吃煎饼了吗”。小孩子在大街上玩,到饭点儿了,大人们在街上喊:“大伟,回家吃煎饼了!”
吃煎饼,卷大葱,就大酱。拿起一个煎饼,向大缸里挖一勺子大酱,连同大酱里一嘟噜一嘟噜的青花椒,一起抹进煎饼里。煎饼宽大的肚膛里再撸上一根大葱丶几根长长的豆角,一起卷上,一口咬下去,“咔嚓”作响。我吃过煎饼,也就过大葱,但是大酱丶花椒不常得。真盼着什麽时候能够凑齐这几样东西,轮起一个煎饼,大口大口地猛吃一气,让大葱的辛辣在额顶上嗡嗡作响,让嘴巴里充斥着青花椒的鲜麻和大酱的浓香。
我妈妈也晒过大酱,她用发霉的煎饼,放在瓷盆子里,加上盐,放在我家东边那半截屋框子上晒。这样晒出的酱,像老红糖一样,浓浓的丶沙莹莹的,是我记忆中最有味道的大酱。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在娘家每天出去种地,享受不到在家做饭的待遇,就没有烙煎饼的“童子功”,以致于她出嫁以後不会烙煎饼,烙出的煎饼很厚。不好吃,但是压饿。一个大大的煎饼卷儿里头,抹上一勺大酱,青辣椒撕开,让它躺在煎饼宽敞的胸膛里,一起卷上,就是妈妈一顿饭了。妈妈爱吃生鲜的东西。走在田间地头上,有伸出头儿的长长的豇豆角儿丶绿豆角儿,她伸手摘下,“咯吱咯吱”地吃起来。
我爷爷奶奶都比我妈妈会做饭。我奶奶烙煎饼的时候,常常趁着热鏊子,做菜煎饼吃。奶奶把大白菜丶红辣椒剁成馅子,在煎饼快要烙好的时候,往上倒上拌好的馅子,在鏊子上摊摊,馅子熟了,把整个煎饼在鏊子上卷起来,卷成一个长长的带菜的煎饼卷儿。把煎饼卷儿,拿到菜板上,一段段切开,就是一块块的菜煎饼了。这样的菜煎饼,外面是香香脆脆的刚烙好的煎饼,里面是新鲜的白菜丶辣椒,咬一口,鲜鲜的丶辣辣的。
关于菜煎饼,还有一段“家”话。一天,我奶奶烙煎饼,爷爷在鏊子边等着吃新煎饼,本来一切都很开心。可是不知怎的,爷爷奶奶却吵架了。等我看到的时候,她们已经结束了战争。奶奶站着,手里攥着头,眼里含着眼泪,正在跟劝和的邻居老娄奶奶说理。“我做了一个菜煎饼,要给省儿吃的,让他等下一个。他就是不行,非要争着吃!”为了一块菜煎饼,他二人争吵不休,大动干戈。我爷爷好吃,年轻的时候就爱吃独食。儿女长大了都不孝敬。“没用!馋狗不肥!”我妈妈说。
麦口过後,我奶奶又烙了新麦子做的煎饼。咬一口,满嘴儿的麦子的味道。奶奶说:“我烙的这个麦煎饼,没有咸菜也吃的喷香!”奶奶说的是实话。可是,哪家敢天天吃小麦煎饼呢,哪家有那麽多小麦呢?家里的粮食不够吃,就去逃荒,甚至去要饭。
印象里有一个老男人,杜村的,身材高大,右手拿着要饭棍,左边肩膀上背着一个胶丝袋子。要来的煎饼丶馒头,沉落在袋子底。袋子装不满,长长的袋子口儿绕过肩膀,耷拉在左胸前。袋子口儿上系着一个茶缸子。有的人家给他的汤水,他可以盛在茶缸子里,端在手上,边走边喝。
他端着茶缸子,拉着根要饭棍子,到人家门儿上,低着头,眼光偏向门框那边,目不斜视,笑眯眯地丶细声细气地说:“姐姐别生气,姐姐别生气!”他的谦逊的眉眼里又带着点善意的丶因为打扰别人而略显愧疚的笑容。那种笑容让人很难生气或者拒绝。小孩子见了要饭的就跟着看。“叫花子!”他们笑着说。每逢谁家办喜事,要饭的就来了,他们买挂小鞭,到主家门上,“噼里啪啦”放了鞭炮,再找个搭档喊喊好,门里头就有人出来,端着鱼肉,拿着馒头,送到要饭的手里。
那个年代,能吃上鱼肉丶白馒头,是我们这些小孩都要眼馋的事。有一天,一个老女人来庄上要饭,她看起来也就五十来岁,甚至还不到六十岁,年纪跟我奶奶差不多。她从头到脚穿着跟我奶奶一样的蓝衣裳,只是她的衣裳比我奶奶的新一点,她收拾的比我奶奶干净一点。我奶奶在庄里看到她,友好地跟她搭话儿。
“要够吃头儿了?你吃饭了吗?”我奶奶客客气气地问她。
“还没吃。正准备找个肃静地方吃的。”她说。
“到俺家喝口儿茶吧?”我奶奶说。
“行!”她就跟着我奶奶一块儿到了我奶奶家。
该吃晌午饭了,她从她的袋子里拿出来半个白馒头,而我跟奶奶要吃我们的山芋。
“你去吃山芋去吧,省儿。到晌午了。”我奶奶跟我说。
“哦。”我嘴里答应着,心里想的是那个老太太手里的白馒头。她会不会出于友好也给我半个馒头吃吃呢。可是,没有。她自顾自地吃她自己的。
我看看奶奶堂屋桌子上酱色的瓷盆子。瓷盆子里头装满了小山芋。那些小山芋羔子,个个儿都是小手指头那麽大,一个个小巧玲珑,刚煮好,盛了满满一大瓷盆子,还带着热气,像是一个个紫色的小老鼠,本来吃起来应该很香甜的。可是我看着那个女人吃着要来的白馒头,我的心里痒痒的,瞬间觉得我奶奶桌子上的那一瓷盆子的山芋不好吃了。
那个老女人吃着白馒头,看着我吃山芋,她的眼神儿里满是对自己的正确道路的认可,和对我手里的山芋的鄙夷。而我,卑微的拿着山芋,很羡慕她能舍得下脸来出去讨生活。我简直要跟她一起去了。是的,我有点想跟着她一起去,一起到人家的门儿上,也去向人家讨一个白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