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夜小说>制霸一方是什么意思 > 第549章 他们不用仪器收靠人记(第1页)
第549章 他们不用仪器收靠人记(第1页)
“地下赫兹频段,出现反向谐波!”姚小波兴奋地喊道,“这就像……某种‘安抚信号’!”
郑卫东死死地盯着屏幕上的曲线,沉默良久。
“暂停注浆。”他缓缓放下对讲机,语气坚定地说道,“再观察十二个小时。”
“郑总工,您……”项目组负责人还想说什么,却被郑卫东一个眼神给瞪了回去。
深夜,b区自动监测系统记录到了一次短暂的逆向位移。
地基,竟然自行回弹了o毫米!
地质专家连夜复核数据,确认并非人为干预所致。
原来,b区下方存在一条古老的河道沉积层,具有一定的弹性记忆功能。
只要避免持续的高压扰动,它就能自主调节地基的应力平衡。
“妈的,这简直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专家忍不住惊叹道。
天亮前,赵工悄然离开了b区,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
第二天,郑卫东在巡查时,意外地现通风口外多了一小堆黄沙。
黄沙被细心地排列成一个环形,环形的正中央,赫然嵌着那半块带着岁月痕迹的老地砖。
他蹲下身子,默默地注视着那堆黄沙和那半块地砖,心中百感交集。
“老郑,看啥呢?”陈砚田走了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郑卫东没有说话,只是指了指地上的黄沙和地砖。
陈砚田也蹲下身子,仔细地看了看,随即咧嘴一笑:“呦,这是……交给下一段路?”
郑卫东点了点头,站起身,抬头望向远方,意味深长地说道:“是啊,交给下一段路……”
姚小波扛着摄像机,默默地记录下这一幕。
一周后,“动静结合巡检模式”正式写入省级市政技术导则。
但在那密密麻麻的条文附录备注栏,一行略显潦草的手写字迹格外醒目:“建议保留局部未硬化路面,供人工触诊使用。”
于佳佳扫过那行字,嘴角不禁微微上扬,笑了。
她太清楚这背后的意味了——这是体制能给出的,最大的妥协。
就像挤牙膏,能挤出一点,就绝不客气。
当晚,华灯初上,她拎着一个略显笨拙的陶罐,悄无声息地回到了步行街东口。
借着昏黄的灯光,她小心翼翼地将那块饱经风霜的老地砖,轻轻地放回了井盖边缘。
触手冰凉,带着泥土特有的潮湿气息。
凌晨三点,空旷寂静的街道上,只有摄像头尽职尽责地闪烁着红光。
监控画面清晰地记录下一道佝偻的身影,步履蹒跚地走近那处井盖。
那人影弯下腰,动作娴熟地从一个布袋里掏出一块新的地砖,然后如同变魔术般,将两块砖迅完成了交换。
新的地砖,纹路与老砖惊人地相似,重量也几乎一致,仿佛是从同一个古老的窑炉里烧制出来。
可是,档案里明明记载着,那座窑,早在年就塌了。
随着一声叹息,人影又缓缓消失在街角的阴影里。
几天后,于佳佳又在东口遇见了赵工。
她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问出了口:“赵工,那砖……”
赵工停下脚步,转身望着她,那双饱经沧桑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芒。
“丫头,你觉得,啥是真,啥又是假呢?”他轻声问道,声音低沉得像是在自言自语。
于佳佳一时语塞,她感觉自己似乎触碰到了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却又无法言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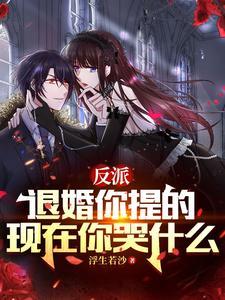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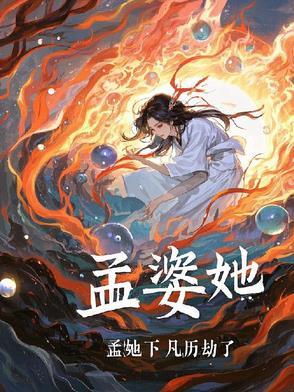
![钓系美人深陷修罗场後[快穿]](/img/16862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