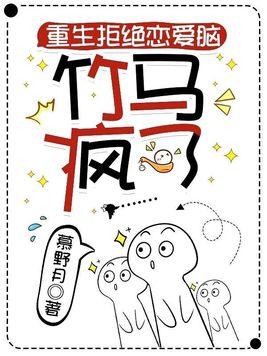紫夜小说>和克里斯 > 5 9(第2页)
5 9(第2页)
那动作流畅而寻常。
“走吧,弗瑞,”她的声音对我笑了笑,“老滴答该等急了。”
她没有探究,没有评论。
我的心沉了下去。那沉,并非坠入冰窟的刺骨,而是一种带着钝痛的明了。
梅尔小姐的匆匆离去……她那些神出鬼没的本事……简冰冷高效的行事风格……
我该问吗?
问什麽?
“简,是你和梅尔做的吗?”
为了我?为了我的家人?为了那些无辜死去的人?
问不出口。
我信任简,近乎本能地信任她。这种信任,在生死之间已经深深扎根。
也许,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答案。
她的沉默。
我的沉默。
我想到了倒在泰晤士河畔的杜维恩伯爵。
我最终什麽也没问。
只是沉默地跟在她身後,踏上公寓的台阶。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清脆地响起,门内传来老滴答熟悉的嘟囔声。
公寓里弥漫着熟悉的灰尘和柠檬油混合的味道,阳光透过窗户,在地板上投下温暖的光。
一切似乎都和离开时一样。
简脱下大衣,挂在衣帽架上,动作依旧利落。她走向窗边,望着楼下逐渐喧嚣的布鲁姆斯伯里街道。
阳光照在她棕色的头发上,泛着一层柔和的光晕。
“弗瑞,”她没有回头,声音很轻,几乎要融进窗外的市声里,“伦敦的雨,总是能洗刷掉很多东西。”
我站在玄关,望着她的背影。
那背影挺拔,熟悉。
洗刷?洗刷掉血迹?洗刷掉痕迹?还是洗刷掉……记忆?
她是对的。
伦敦的雨很大。
雨水会冲刷石板路上的污迹,会模糊行人的视线,会将一切尖锐血腥的东西,都溶解在它灰蒙蒙的丶永无止境的潮湿里。
我们不会再提起萨罗郡那只猴子的真正来源。不会再深究利德森叔叔背後那只更阴冷的手。也绝不会,去触碰报上那几桩发生在殖民部大楼阴影里的割喉惨案。
真相,它们会像被雨水打湿的墨迹,晕染开,最终只留下一个模糊且令人不安的印子。
我走到她身边,也望向窗外。
春日的气息仍在,泥土的芬芳,新叶的清新。
梅尔小姐在哪儿?也许在某个烟雾缭绕的角落,也许已经踏上了去往下一个目标的火车。她像一道无声的影子,执行着简那冰冷而高效的意志。
而简……我侧过头,看着她平静的侧脸。
那浅绿色的眼睛深处,映着窗外伦敦铅灰色的天空,深得像不见底的寒潭。
信任,有时就是一场沉默的共谋。
为了走下去,为了那些她承诺会保护的人,包括我,也包括纳迪尔,包括许许多多的人。即使这信任的基石下,可能铺着未冷的血。
“是啊,”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响起,平静且清醒,“伦敦的雨……总是很大。”
窗外,一片阴云缓缓遮住了阳光。
第一滴雨,终于落了下来,敲打在玻璃窗上,留下一条蜿蜒的水痕。
像是谁的眼泪,又像是冲刷一切的开始。
那报纸上惊悚的标题,那几位官员离奇而惨烈的死亡,它们究竟是谁的手笔?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至少,在明面上,在弗瑞和简之间,在她们奔赴的下一个案子之前,它们只会是伦敦又一个被雨水冲淡的丶悬而未决的谜。
雨,渐渐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