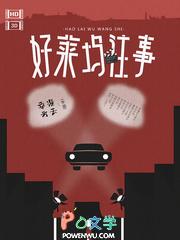紫夜小说>你不是朕的白月光 作者石门之客 > 第47章 第四十七章 看见了浴池水下的风光(第3页)
第47章 第四十七章 看见了浴池水下的风光(第3页)
却想起了长门怨中的两句“张罗绮之幔帷兮,垂楚组之连纲”①,忙又放下了幔帐。
干脆合上了眼。
耳边是更漏滴答,北风敲着窗棂,使人想起了宣室殿的长夜与甬道。
那个时候看来,还是很有趣的。
她看着对面的户牖,映出人影,先是小小的,远远的,嵌在窗纱上,像极了夜深不眠的鸱鸮。
一会儿,近了近了,人影也随之变大了,变宽了,纱上的光晕毛茸茸的,就将那人影变成了山君。
有时候他拆了束发,长发散落在风里,看起来又成了狻猊。
上林苑的虎啸狮吼,声声入耳。
入梦而来的狮身虎身上,都长了噙着笑的人脸。
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她趿了鞋子,起身沐浴。
水气氤氲,偏室中茫茫一片,像极了锅子的热气。
她生平吃过最难吃的锅子,就是在紫宸阁里。没有尝到肉味,只吃到了芜荽。
唉,该死啊,一顿火锅而已,她怎麽就释怀不了了呢?
快一年了,怎麽想起来,还是涩,还是苦,还是痛,还是痒呢——竟让人想哭了呢?
她把脸埋入了浴桶的水里。
青丝像水草一样漫开。
她伸出手指,绕着发梢,总算想起了其他的事。
是及笄的那一日,阿母为她篦发,梳过一遍,眼眶中的泪水就盈满一点。
“阿母怎麽不高兴呀?”她歪了歪头问,“是觉着我挽髻不好看吗?”
“哪有?我们家阿鸢多好看。整个东平乡里,最好看了。”阿母嗔怪,抹去了眼角的一滴泪。
“这是高兴,阿鸢长大了,到了可以嫁人的年岁了。”
“阿母,你说,我会嫁一个什麽样的人?”她兴致勃勃地问。
“阿鸢定会嫁给一个喜爱你,疼惜你的人。”
阿母开了口,就意犹未尽,对着镜子里的林鸢,开始一点点勾勒起这个喜爱与疼惜她的人的模样。
“身量要高,高大威猛的,可以护着你。”秦氏想了想,又摇摇头,说,“但也不能太高大太威猛了,免得没轻没重,伤到了你。”
“还有,模样要好,看着顺心,饭都能多吃下两碗。”她稍一思量,转而道,“但这模样也不能太好——”
林鸢不解:“阿母,你难道是觉得我本来就吃得够多了吗?”
一旁的林榆笑喷了茶,秦氏轻咳了一声,嗔怪:“不然,总会被人肖想。那多不好。”
“就像林榆那样吗?”她哈哈大笑,引来了林榆侧目。
秦氏挺直了腰杆,眼里闪着自豪:“那是。我们阿榆样貌学识统统都是万里挑一,让多少人肖想都是该的。”
林鸢来不及从秦氏的神色中想明白,这被人肖想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又听秦氏说:“你以後嫁的人呐,最好是当官的,有一些家底。家里得有下人,毕竟,你不会刺绣,又不会织布,不晓得养蚕,也不会种地……”
“有一些家底,看来也够呛啊。”林榆幽幽道。
林鸢捶了林榆胸口一拳。
秦氏说得口干舌燥,补充:“所以,这官不能太小,太小了,下人不够多,农忙的时候,连帮佣耕都不忙不过来。”
她想得发了愁,“不过,这官也不能太大,太大了,那种王公贵族,王侯将相的家,家中人多,不好管家,族里亲眷也多,规矩大得很,咱们是农户人家,小门小户的,将来嫁过去了,保不齐受人欺凌,到时候,想为你出头也没法子呀!”
“这个啊,阿母大可放心!”林鸢忍不住插嘴。
秦氏朝她看了过来。
林鸢手一摆:“我们农户人家,方圆百里,都没有什麽王公贵族,掰着手指,上数五代,都不识得什麽王侯将相,阿母就不必担心人家来提亲了!”
她说得扑哧直笑,伸出手,抚平了秦氏担忧而紧蹙的眉头,“担心人家规矩多,还不如担心人家纳采礼多,咱们小门小户的,摆不下呢。哈哈哈。”
秦氏充耳不闻,沉浸在对未来女婿的遐想中,继续说:“年岁呢,不能太大。顶好大你两三岁,年岁太小了,不懂事。太大了,就会觉得你不懂事……”
林榆抱胸不语,林鸢捂起了耳朵。
脑中占满了另一段回忆,另外的人,她的唇角随之勾起。
只是,她最後没有嫁人,却入了宫。
“呼——”
湿发甩在了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