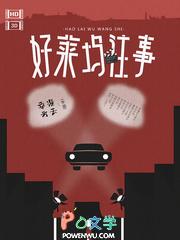紫夜小说>你不是朕的白月光 作者石门之客 > 第47章 第四十七章 看见了浴池水下的风光(第4页)
第47章 第四十七章 看见了浴池水下的风光(第4页)
她从浴桶的水中扬起了脸,换了一口气,也及时地刹住了神思。
眼前,是萧珣的胸膛,他的手臂枕在她的脑後。
方才,就在快要一头撞到池底的时候,她看见池壁上盘着的龙活了过来,一个摆尾,托住了她的脖子,接着托住了她的腰。
萧珣看着林鸢。
她的衣裳贴在身上,只因从厢房相连的廊道过来,萧珣早教人在那里连廊的两侧挂好了厚厚的帷幔,隔了风雨,隔了寒气,屋中炭火旺,加上来时匆忙,所以她穿得并不厚。
在水中透湿,那衣裳几乎变成了与去岁的夏日一样的轻衫。
她正大口喘着气,胸口起伏不止。
淮阳王府东苑的浴池,径有两丈,连的是一个天然的温泉。
热气氤氲,云雾缭绕,显得水面茫茫。
他的神思一时迷离。
是梦吗?
他离她那麽近,揽着她。
他的身子很热,揽着她的手丶手臂隔着遇水变薄的衣衫烧灼着。也像极了那个夏日。
仿佛,他们之间没有隔着那食不甘味的五个月。
五个月,每一日,他习惯地推开窗,看向西偏殿的户牖,那里黑沉沉一片。
她这个时候在干什麽呢?
在揽月阁的灯下看书吗?在那檐下看星星吗?早早安寝了吗?人参与鹿茸熬的汤很苦,没有他督促着,她乖乖喝了吗?
天冷了,她加餐了吗?起风了,她添衣了吗?
月出皎兮,月为什麽照不出她的身影呢?
照不见她,月也昏昏,星也昏昏。
宣室殿正殿西侧的户牖,开了又合,合了又开。
多少个时日,他都快数不清了。
日子啊,日子,能不能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
箭矢飞得再迅疾一些吧。长剑挥得再有劲一些吧。铁蹄踏得再猛烈一些吧。战鼓击得再嘹亮一些吧。
他要带着胜利的捷报,飞到那山巅上去,去接她回来。
可是,见不到她的日子里,那些夜啊,夜啊,能不能过得慢一些,再慢一些?
到了最深的夜,他能见到她了。他是那麽不舍,不舍那最深的梦,不舍得醒来。
梦里,他搂着她,月色皎皎,星辉缭乱,云卷云舒,雨露沾裳。
就像眼前这样。
她伏在他的臂上,靠着他的膝头,长发如瀑,垂在两肩,眼眸氤氲,睫羽沾露,嘴唇盈盈发亮,像极了透红的樱桃。
他的心怦怦直跳。
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去。
是他的梦。
是他错过了半年的夏天啊。
云母屏後倏忽传来了细微的声响。
只见影影绰绰一个人影,弓着腰,手上举着托盘,慢慢地後退,後退,远了。
李顺听见里面的水声哗啦,又见汤池的水几乎汪到了屏风与衣笥之下,早已慢下了脚步。
屏风透光,仔细看去,隐约可见人影交缠。
他忙低下了头,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蹑手蹑脚地退出去。
澡豆和沉香,却在金质的托盘里乒乓作响。
林鸢扭过头去,醒过了神。
“你方才是想叫李顺进来的,是不是?”她仓皇说着,伸手扶向池沿,向旁退了两步,远离了他,“我,我不熟悉路,走,走错了。你,你的伤口,好像,又裂了。”
她看向他的小臂,绑在上面的白色布带,浸成了红色,一滴一滴往下滴着粉色的水。
“哦,没事儿的。”他望着臂弯里空荡荡的水面,舔了舔干燥的唇,悻悻一笑,“你这不是急着来汤池为我换药来了吗?”
林鸢不解:“不是你拉的铃,让我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