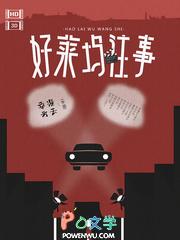紫夜小说>你不是朕的白月光 作者石门之客 > 第47章 第四十七章 看见了浴池水下的风光(第5页)
第47章 第四十七章 看见了浴池水下的风光(第5页)
他茫然:“我在沐浴,怎麽拉得铃?”
一片寂静。
凝神听去,风声大作,依稀间杂着遥远的铃声,叮叮,当当。
萧珣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迎上了林鸢的瞋目。
“我忘了,会有风。”
他喃喃。
林鸢咬着唇,忍着心中郁郁之气,那唇红得能滴血。
眼前的人脱下了纹章华服,发髻亦是松松,没有冠冕,只插了一个玉笄,他让她将自己当作普通人,因而她只想狠狠揍他,踹他。
她现下这般落汤鸡似的狼狈,皆是拜他所赐。
谁让他想出来什麽拉铃铛的鬼主意呢?谁让他大半夜的,还非要沐浴呢?
做噩梦麽?这才是噩梦。
是风吗?呵,她简直要疯。
可拳头在水下攥紧了,一见他赤着的胸膛就泄了气。
更别说踹了。
水汽卷了又舒,水波折过来了水下的风光,想到那水下也是赤的,她的腿都软了,双手打颤,拳头也捏不紧了,不禁向旁又退了两步。
“这池子太深了。”她眼睛不知往哪里看,口中也不知所云。
别过脸去,半晌才道,“还是,谢,谢谢你救了我。”
说着,脚尖总算摸索到了池底,哗啦起身,才发觉水不及腰。
“嗯。水太深了。”萧珣痴痴地顺着她的话应道。
她觉得讽刺,耳梢发热,转身离开。
一身的水,湿淋淋,沉甸甸。
身子泡在热水中有一会儿了,有些脱力,没有踩稳水下的石阶,一个踉跄。
“小心。”
身後,随着水声哗啦骤响,腰碰上指尖的一瞬,“别!别!”林鸢尖叫出声,连声道,“别动,别碰我,不要碰我。”
她唯恐萧珣起身来扶。
方才在水中,闭眼不及。以至于,现在睁眼闭眼都是他的身子。
不不不,她看见的,分明只是活了的龙,颜色白皙,身姿矫健,鳞甲鳞次栉比,垒在腰腹。
腰腹之下,水光折射过来的腿,长的长,短的短,坚实遒劲,曲直有度。
可是,龙,有腿吗?
有几条腿?
她不敢回头,脸红得像要渗血。
手脚并用,落荒而逃,奔向了岸上。
“这麽嫌我碰你啊。”身後的声音低笑着,自嘲了一句。
这话音夹在林鸢湿漉漉的脚步声里。
那脚步声趿拉着水声,很快轻了,远了。
唯独她的身後,那伸出的手还悬在原处,直到上面的水滴成串,冷了,刺骨,才缓缓地垂落回了水里。
汤池激荡起的涟漪,打碎了面上的笑。
恓恓惶惶。
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五个月里,他守着他的梦。
可这是清醒的梦,他深知是梦,所以有时候,还是会害怕醒来的那一刻。
就像天狩三年,阿母死後的很长一段时间,他接受不了阿母的离开,所以害怕每一天的天亮。
天亮了,会看见身边空空荡荡,什麽都没有。
梦里越暖,醒来就越是冷。梦里越是有人相伴,醒来就越发孤单。
而那段时日之後,他的梦,索性也是孤清的,也是冷的了。
假如,假如,是那一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