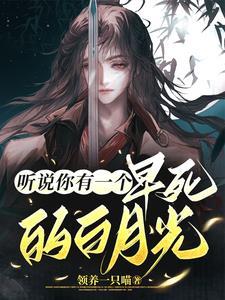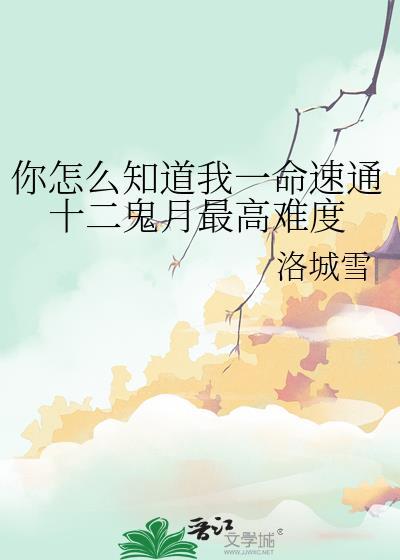紫夜小说>四合院我是雨水表哥 > 第80章 郎氏宗谱(第1页)
第80章 郎氏宗谱(第1页)
这一觉,吕辰直睡到下午两三点,去吴奶奶家转了一圈,看了看吴老太爷,小雨水也陪着吴家小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吕辰交代完。
回家提着一个用棉布帘子盖着的木桶,又小心拿出一个蓝布包裹扁盒,骑着自行车,熟门熟路来到了郎爷家所在的胡同。
推门进去,庭院寂静,那几竿翠竹覆着一层薄雪,更显苍劲。正屋书斋的窗户透出温暖的光晕,映在清扫过的青砖地上。
吕辰在门口跺了跺脚,扬声唤道:“郎爷,我来了。”
“进。”屋里传来郎爷慵懒的声音。
吕辰掀开厚棉帘进屋,郎爷正坐在临窗的桌案后,架着一副老花镜,拿着一柄放大镜,正细细审视着一页脆黄的书叶。
见吕辰进来,他略抬了抬眼,“哟,今儿个还带了东西?又是什么新鲜吃食?”郎爷放下放大镜,身子微微后靠,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自己找地方坐。”
吕辰笑着将木桶放在门边,这才走到书案前,将那个蓝布包裹的扁盒双手放在了郎爷面前。
“快过年了,给您送点年礼。”吕辰语气轻松,带着晚辈对长辈的亲近,“桶里是五只江浙来的大蟹,个头还行,让您尝个鲜。主要是这个……”他点了点那蓝布包裹,“想着或许您会感兴趣,就给您带来了。”
郎爷的视线落在扁盒上,眉毛微不可察地动了一下,伸出干瘦却稳定的手,解开了蓝布包上的活结。
布包散开,露出里面一个略显陈旧的木匣。木料是普通的樟木,做工也寻常,但边角磨得光滑,显是常被摩挲。匣子没有锁,只用一个简单的铜扣搭着。
郎爷打开铜扣,掀开盒盖。
里面静静地躺着一函线装书。蓝色的土布封面,纸捻装订,显得朴素甚至有些粗陋。封面中间贴着一张小签,上面是工整的墨笔楷书:《婺源郎氏宗谱》。
“宗谱?”郎爷低语一声,目光在那“郎”字上停留了一瞬,随即看向吕辰,带着询问之意。
他并未立刻去动那函谱,只是用指尖轻轻拂过封面边缘,感受着纸张的质地。
“嗯,”吕辰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前两年,帮我们修缮房子的周师傅牵线,得了些旧书。是从一位刚去世的莫羡云莫老夫子宅里流出来的。老夫子膝下子侄都在南方,回来处理丧事,带不走的书籍旧物就托周师傅处置。周师傅知道我好这个,就叫了我去。这函族谱,就是从那堆书里得的。”
郎爷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那“郎”字上敲了敲:“莫羡云……老夫子?那位精通明史,尤擅钦、徽二州典故的老学究?”
“正是他。郎爷您认识?”
“谈不上认识,闻其名而知其学。”郎爷语气平淡,但眼中闪过一丝惋惜,“是他的话,手上有徽州人家的族谱,倒也不奇怪。婺源,古属徽州府,文风鼎盛,宗族观念极重,几乎姓姓有谱,家家有祠。”
他的目光重新落回那函谱上,这次,他小心地用双手将谱册从匣中请出,平放在铺了一块软毡的桌面上。动作轻柔舒缓,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婺源郎氏……”郎爷喃喃自语,像是在记忆中搜寻什么,“这个姓氏,在婺源似乎并非大姓巨族,但也源远流长。我记得……其先祖可追溯至五代时期,为避战乱,自中原迁入徽州,聚族而居于婺源西北部的郎川河谷一带,世代耕读传家,明代中后期似乎还出过几位举人、进士,在地方上也算得上诗礼之家。”
他一边说着,一边极其小心地翻开封面。扉页之后,是历次修谱的序言,墨迹深浅不一,笔迹各异,记录着时光的层叠。
“战乱啊……”郎爷声音低沉,带着感慨,“尤其是近几十年,太平军过境,北伐抗战,中原板荡,江南亦未能幸免。多少传承数百年的宗族谱系,毁于兵燹,散于离乱。能保存下来的,十不存一。这莫老夫子能收藏此谱,想必也是费了一番心思,或许与郎氏族人有些渊源,或许只是治史者的搜集癖好。”
他轻轻抚过一行记载着明代某次修谱的序文,纸张脆薄,仿佛一用力就会碎掉。“徽州人家,视族谱为根脉所系,比性命还重。寻常绝不肯示与外姓。非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让家族之宝流落在外。此谱既到了莫老夫子手中,又辗转至此,想来,婺源郎氏本家,怕是经历了不小的劫难,甚至可能,族运衰微,香火零落了。”
说到这里,郎爷忽然停顿了一下,抬眼看了看吕辰,那双总是半眯着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极为复杂难言的情绪,有好奇,有追忆,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他状似随意地问:“这谱,你翻看过吗?可知其记载至何时为止?郎氏如今境况如何?”
吕辰注意到郎爷的情绪变化,心中微动,答道:“粗略翻过一下。此谱最后续修,似乎是在光绪朝中期。后续似乎也有零星的墨笔添注,但看上去止于民国初年。再往后便无续修的记录了。至于郎氏现状,我确实不知。”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郎爷沉默地点点头,目光重新沉入纸页中,极其专注地,一页页地慢慢翻阅。时而用放大镜仔细辨认模糊的字迹或印章,时而手指在某个人名或年代上停留片刻。书斋里只剩下纸张翻动的轻微沙沙声。
吕辰也不打扰,静静地坐在一旁,他知道,对于郎爷这样的人,这样一函跨越时空、承载着一个家族记忆的故纸,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时间悄然流逝,直到窗外天色开始泛灰,郎爷才缓缓合上谱册。他长长地、极其缓慢地吁了一口气,仿佛将一段沉重的历史轻轻放下。他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眉心,脸上带着一种沉浸在往事中的疲惫与感慨。
“光绪二十三年,最后一次大修。”郎爷的声音有些沙哑,“添注止于民国四年,郎鸿昇之三子出生。其后便是空白了。”
他抬起头,像是在对吕辰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郎川河,郎家村,祠堂门前有一对石鼓,据说是某位中了进士的先祖立的。村口有棵老樟树,七八个人才能合抱,这些,谱里都有图记记载。看来,彼时族运虽不及明末清初时显赫,但人丁还算兴旺,根基犹在。”
“只是这后来的空白……”郎爷摇了摇头,语气沉痛,“民国肇始,便是乱世。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徽州虽处山地,也难逃波及。尤其是抗战时期,婺源几度易手,多少村落被焚,多少家族流散,这郎氏宗谱后续无记,只怕……。”
他没有说下去,但那沉重的猜测已很明显,一个可能延续了数百年的家族谱系,或许就在那时代的巨变中,戛然而止,散落湮灭。
良久,郎爷才从思绪中回过神来,眼神恢复了清明,但却涌动着激动和探究。
“小吕啊,”他声音很低,带着颤抖,“你可知,老夫祖籍何处?”
吕辰心中一跳,一个隐约的猜测浮上心头,他谨慎地回答:“只听您提过祖上在前清宫里校书,却未曾听您说起祖籍何方。”
郎爷的目光紧紧盯着吕辰,一字一句地道:“老夫祖上,正是婺源郎氏。康熙朝中期,一支迁入顺天府。至我曾祖,入选内府校书郎,此后三代,皆以此职侍奉宫廷。家中原本也藏有一部《婺源郎氏宗谱》,乃是迁京之时,本家所赠,与族中各地支脉所持之谱同源而出,详略或有差异,但世系源流一般无二。”
他呼吸急促,眼中闪过一丝痛楚:“那部谱,连同家中无数藏书,在庚子年那场大乱中,尽数毁于一旦了。那时我还年幼,只记得家中烈火熊熊,祖父顿足捶胸,泣血哀嚎,那是我郎家京支传承之根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