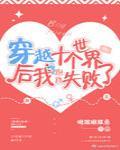紫夜小说>破帷的意思 > 第188章 缝里长出的不是字是胆(第2页)
第188章 缝里长出的不是字是胆(第2页)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陶炉里的炭火烧得正旺,她将纸页投进去,火星子“噼啪”炸开,焦味混着槐花香窜进鼻腔,呛得人眼酸。
“他们撕衣而出的不是字,是敢说‘不对’的胆。”她望着跳动的火苗,声音里带着淬过的钢,“可若我们还等着他们来问,便是我们输了。”
阿梨突然拽她衣角:“阿昭姐,输了会怎样?”
她低头,看见孩子眼里映着火光,亮得像星子,烫得她心头一缩。
“输了,他们就会把‘问’字重新缝回布缝里,把‘胆’重新锁进喉咙里。”她摸出块青石板,用炭笔在上面画了个张开的嘴,炭粉簌簌落下,像灰烬重生,“真正的思想,要长在喉咙里,不是纸上。”
当夜,程知微的亲随裹着露水叩门。
林昭然正借着月光抄写《波问录》,墨迹在宣纸上洇开,像片要漫出来的云。
亲随递来刻着密文的竹板:“程先生说,最后一章若是写成书,不出三日就会被稽查司抄走。他问,改成口传如何?”
她将笔搁在笔山,墨汁沿着笔锋滴成小圆点,像一颗凝住的泪。
她想起白天焚书时,阿梨攥着她的手说:“我记着‘有教无类’呢,阿昭姐教过的,我能说给我娘听。”
“改。”她抓起竹板,在背面重重写了个“传”字,炭粉飞扬,“只传不写,口口相授。真正的思想,该像风——你堵不住风,只能被风吹着走。”
——同一轮月下,岭南晒谷场上,阿梨仰头望着同样的天。
里正扯着嗓子喊“免税三年”的政令,唾沫星子溅在新贴的黄榜上,黏腻亮。
三十七个村民蹲在草垛边,有的搓着草绳,有的哄着怀里的娃,没人抬头。
“都听明白了?”里正拍了拍黄榜,竹板似的响,“三年后……”
“三年后呢?”
童声像根细针,刺破了暑气的闷。
阿梨从草垛后钻出来,小短腿颠到中间,仰着脸:“十年后呢?你们说免税,可没说免账。”他裤脚的泥还没干,踩在地上留下一圈湿印。
晒谷场突然静了。
老周头的烟袋锅子敲在青石板上:“前年春荒,借官粮一石,利三斗。”
阿秀嫂把娃往肩头挪了挪,声音细如游丝:“去年涝灾,借种粮半石,利二斗。”
“今春修渠,摊丁银五钱,利一钱。”
三十七张嘴,三十七种声音,却像合了律的琴,将十年的账册明细诵得一字不差。
空气里浮动着汗味、草腥与压抑已久的怒意。
山岗上,程知微攥着腰间的盐囊,指节白。
日光透过树叶洒在他脸上,将他眼底的震骇切成碎片。
那些他在盐场教的“一担盐换三碗米”,在田埂教的“春种一粒粟”,此刻都从百姓的喉咙里涌出来,成了最锋利的刃。
“索权……”他喃喃自语,盐粒在囊里沙沙作响,“原来不是我们在教他们,是他们在教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有教无类’。”
而在京中,沈砚之正对着新送的《舆情地脉图》皱眉。
图上的“岭南道”本该是密密麻麻的红点,此刻却成了一片空白——那是百姓不再用嘴说话,改用行动说话的区域。
“音律可察悲欢,五音乱则心不宁。”他低声说,指尖划过“静默”二字,“百姓不言,未必无怨——记他们说话前的喘息、话尾的顿挫,或许比言语本身更真。”
提举颤声回应:“奴才们试着听巷口茶摊的闲谈,现近来人说完一句话总要愣半晌……像是等着谁接,又没人敢接。”
三日后,裴怀礼跪在丹墀下,朝服沾尘,奏疏被攥得皱:“若连沉默皆需审查,则天下再无真心!”金殿蟠龙柱投下阴影,罩住他挺直的脊梁。
沈砚之垂眸看他,像看一块撞向石壁的顽石。
“裴少卿,”他的声音裹着殿角铜铃的轻响,“你见过被洪水冲垮的堤坝么?不是因为水太猛,是因为缝太多。”朱笔掷下,墨迹晕开,像朵妖异的花,“准奏。”
风过处,处处是缝,处处是问。
喜欢破帷请大家收藏:dududu破帷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