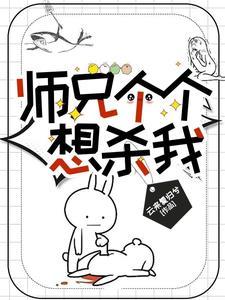紫夜小说>今天小狐狸吃鱼了吗? > 狼子痴心帝心微澜(第1页)
狼子痴心帝心微澜(第1页)
狼子痴心,帝心微澜
凌延还是不放心,于是让亲信务必将何知洲带回来。他自己被盯的紧,只能派人一直盯着,心里急的不行。
心思总被牵挂着,难免会疏于防范宗亲。
天牢深处的石壁总在渗水珠,嗒嗒声敲在骨狼的心上。
他捧着刚从御膳房偷来的燕窝粥,指尖被烫得发红却浑然不觉。牢门吱呀开了道缝,安王蜷缩在草堆上的身影撞进眼帘——玄色囚服上的金线被污泥糊成灰黑,唯有侧脸的轮廓,仍带着当年的清俊。
“殿下,趁热吃。”骨狼跪行着把粥碗递过去,少年音里裹着小心翼翼的讨好。
他化形时总爱维持着十六七岁的模样,眉眼精致得像画中仙,只有耳後若隐若现的银灰狼毫,泄露了非人的底细。
安王掀起眼皮,眼底积着化不开的阴翳。他没接粥碗,反而伸手捏住骨狼的下巴,指节用力到泛白:“昨日让你去殿外散布的流言,办得如何了?”
骨狼的下颌被捏得生疼,眼里却瞬间亮起细碎的光,像得到指令的猎犬:“都办妥了。侍卫们都在传,何先生是黑巫教的细作,房山矿脉的戾气是他故意引出来的。还有几个老臣的家眷也在寺庙里求签,说……说妖物不除,国无宁日。”
他说着,忽然舔了舔安王的指尖,舌尖带着狼崽特有的温热黏腻。安王猛地甩开他的手,嫌恶地用帕子擦着指尖,眼底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松动。
这只骨狼是他在北疆雪地里捡回来的。当年他被宗亲们扔进猎场喂狼,是这只幼狼拼死护着他,硬生生撕断了三条恶狼的喉咙。
後来他才知道这是只修行了五百年的骨狼精,能化人形,能嗅出人心底的欲望。
他给了他名字,给了他栖身之所,也亲手折断了他的傲骨——灌下化形丹时,骨狼疼得在地上打滚还死死咬着他的衣角,连一声哀嚎都不肯让他听见。
安王终于端起粥碗,慢条斯理地舀了一勺,语气阴狠的咒骂:“明日早朝,就是凌延的死期。”
骨狼趴在他脚边,用脸颊蹭着他的靴面,像只邀功的宠物:“殿下,等您重掌大权,能不能……能不能把何先生的妖丹给我?我听说,泥鳅精的内丹能治百病,我想……”
“你想什麽?”安王打断他,眼神骤然变冷。
骨狼吓得一哆嗦,慌忙改口:“我想给殿下补身子!殿下这些年受的苦,都该用那妖物的血来偿!”
安王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低笑出声。他伸手抚过骨狼耳後的狼毫,触感柔软得像上好的绸缎:“阿骨,你这颗心倒是对我掏得彻底。”
骨狼的耳朵瞬间红透,连脖颈都泛起粉色。
他知道自己的心思有多龌龊——他不光想撕碎何知洲,还想让安王永远圈养自己,像当年在北疆山洞里那样,只有他们两个人,谁也不能来抢。
可他不敢说,他只能把这扭曲的执念都裹进对安王的绝对服从里。
次日的大殿上气氛比往日更压抑。凌延刚坐上龙椅,就见吏部尚书颤巍巍地出列,手里举着一卷黄纸:“陛下,昨夜钦天监观天象,见紫微星旁有妖星犯主,恐……恐对陛下不利啊!”
“妖星?”凌延的指尖在龙椅扶手上轻轻敲击,“尚书大人是说,何先生?”
“臣不敢妄议!”吏部尚书叩首在地,“但民间流言汹汹,都说何先生是黑巫教馀孽,若不尽快处置,恐生民变啊!”
他话音刚落,二十多位大臣齐刷刷跪了下来,异口同声道:“请陛下诛杀妖物,以安民心!”
凌延的目光扫过人群,落在站在最前排的安王身上。一夜之间,这位阶下囚竟换上了干净的朝服,面色平静地站在那里,仿佛昨日的阶下之囚只是幻觉。
“皇弟怎麽看?”凌延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大殿。
安王出列,躬身行礼,姿态谦卑得恰到好处:“陛下,臣以为,流言不可尽信,却也不可不信。何先生曾护地脉有功,贸然处置,恐寒了天下能人的心。不如……先将他交由臣弟审问,待查清黑巫教之事,再做定夺?”
他话锋一转,语气里添了几分忧色:“只是臣昨日在天牢,听闻黑巫教的锁灵塔就在京城。那法器专□□怪灵力,若被何先生所得,後果不堪设想啊。”
“锁灵塔?”凌延的瞳孔微微收缩。
周显查到的密报里,确实提过这件法器,却没说具体位置。安王此刻抛出这个消息,显然是早有预谋。
“臣也是偶然听闻。”安王垂着眼,掩去眼底的算计继续装傻充愣:“据说那塔是用百妖骨血浇筑而成,若能找到它,或许能解房山矿脉的戾气。”
殿内的大臣们顿时骚动起来。有人主张立刻搜城找锁灵塔,有人坚持先处置何知洲,吵吵嚷嚷间,竟没人再提安王私开矿脉的罪证。
凌延看着这混乱的场面,忽然觉得一阵疲惫。他精心布局,本想今日彻底扳倒安王,却没料到对方会用“黑巫教”和“锁灵塔”做文章,更没料到这些大臣会如此轻易地倒戈。
“够了。”凌延沉声开口,龙椅上的威压散开,殿内瞬间安静下来。
他说:“何先生是忠是奸,朕自有判断。锁灵塔之事,交由周显全权负责,任何人不得插手。”
话音刚落,安王忽然咳嗽起来,鲜红的血沫顺着嘴角滑落。他踉跄着後退一步,像是受了极大的刺激:“陛下……难道臣的话,您一句也不信吗?臣虽有错,却绝无半句虚言!若锁灵塔真被妖物所得,那江山……”
“皇叔不必多言。”凌延打断他,心里却咯噔一下。安王这副虚弱模样,落在群臣眼里,只会显得他这个皇帝刚愎自用,容不下忠言。
果然,几位老臣立刻上前搀扶安王,对着凌延叩首道:“陛下!安王殿下是为江山社稷着想啊!您怎能如此凉薄?”
“臣等愿以项上人头担保,安王殿下绝无虚言!”
“请陛下三思!”
“……”
凌延看着眼前黑压压的人群,忽然想起何知洲曾说过:“朝堂如泥潭,陷进去容易,爬出来难。”那时他还笑他多虑,如今才知,这泥潭里的漩涡,远比他想象的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