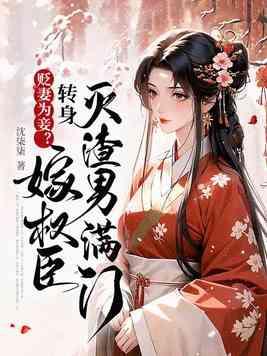紫夜小说>今天小狐狸吃鱼了吗? > 晴日初暖河谷渐宁(第1页)
晴日初暖河谷渐宁(第1页)
晴日初暖,河谷渐宁
雨停後的河谷像被洗过一般,连空气都带着草木与泥土的清新。
凌延踩着半干的红泥往营地走,鞋上沾的泥块被阳光晒得发脆,走一步掉一块碎屑。
刚到营门口,就见何知洲正蹲在柳树下,手里捏着根枯枝,在泥地上画着什麽。
“在琢磨什麽?”凌延走过去,故意加重脚步,看他会不会像从前那样吓一跳。
何知洲却没回头,指尖在泥地上轻轻一点:“你看这里。”
他画的是渠沟与滚水坝的衔接处,用枯枝标出一道弧线。
“之前设计的是直角转折,水流冲击太大,不如改成弧形,让水势自然缓冲。”
凌延蹲下身,视线顺着那道弧线滑过去。
阳光透过柳树叶的缝隙落在何知洲发顶,镀上一层浅金,连他鬓角沾的一点泥灰都显得柔和。
这几日憋在心里的焦灼,像是被晴日晒化的露水,悄悄没了踪影。
“你刚到就不安生。”凌延伸手替他拂去肩头的草屑,指尖触到衣料下温热的皮肤,顿了顿才收回手。
他顿了顿补充道:“先去歇歇,我让夥房炖了姜汤。”
何知洲仰头看他,眼睛亮得像浸了水的琉璃:“比起姜汤,我更想看看你这几日的成果。”
他站起身,折扇往掌心一拍恍然大悟似的:“听说你用柳条筐护渠壁?倒是比古籍里记的‘柴石护岸法’更巧。”
凌延领着他往渠沟走,一边走一边说“那几日雨太大,红泥层泡得发酥,不用柳条捆着,怕是早塌了半截。”
两人并肩走在渠边,脚下的泥路还软着,偶尔踩重了会陷进半寸。
何知洲边走边看,时而弯腰摸一把渠壁的红泥,时而驻足观察新挖的排水沟,嘴里念念有词:“红泥黏性虽好,却怕水泡,等干透了,得在表层掺些砂礓,能防开裂。”
凌延听着他的话,忽然想起怀里的册子:“你送的那几本旧案,我看了滚水坝防渗的法子,铺碎石层再浇桐油,明日就试着弄。”
何知洲停下脚步,转身面对着他说道:这事急不得,先等渠沟彻底干透。你看这红泥,现在还能攥出浆来,强行施工只会前功尽弃。”
他伸手,指尖轻轻碰了碰凌延的脸颊,仿佛在说你眼下还有青黑,一看这几日没少熬夜?
凌延下意识偏头躲开,耳尖却有些发烫:“夜里得盯着渠水,怕再塌了缝。”
何知洲没再追问,只是从袖中摸出个小瓷瓶,塞到他手里:“这是安神的香丸,夜里点一粒,能睡安稳些。”
瓷瓶触手微凉,还带着何知洲身上的清冽气息。
正说着,老河工扛着木尺走过来,见了何知洲先是一愣,随即笑开了:“这位就是何先生吧?凌大人这几日嘴上不说,手里总攥着您送的册子呢。”
何知洲笑着拱手:“劳烦您多照看。”
“该的该的!”老河工笑得眼角堆起褶子,“先生来得巧,刚有人从州府捎信,说京里倒安生了些。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锁灵塔,听说安王已经收手了,只派了几个老工匠去清理废墟,再没调过一兵一卒。”
凌延微怔,随即松了口气。
锁灵塔那场火後,他一直担心安王会借机生事,如今看来倒是多虑了。或许那位王爷折腾了几日,终究还是没敢真动皇家禁地的主意。
何知洲指尖转着折扇,轻声道:“安生些好。京里安稳,咱们这边的石料粮草才顺顺当当。”
他看向渠沟深处,“听说滚水坝要开始砌坝基了?我带的那本《河防考》里有几个省料的法子,正好能用上。”
凌延点头,压下对京中之事的最後一丝顾虑,跟着他往坝基工地走。
阳光渐渐热起来,晒得红泥蒸腾起薄薄的水汽,两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在泥地上偶尔交叠在一起,像被粘住了似的。
坝基工地前,石匠们正围着一堆青石打转。见凌延和何知洲过来,王石匠赶紧迎上来:“大人,先生,这青石硬度够了,就是形状不规则,不好砌啊。”
何知洲蹲下身,捡起块碎青石掂量了掂:“不用都凿成方的啊。你看这石头的弧度,正好能嵌进坝体的转角处。”他拿起块尖顶的青石,“这种的可以朝上,水流冲过来时能分流,减少冲击力。”